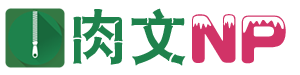血神角斗场。
天穹之上,那道巍峨如山的血神虚影依旧屹立,遮天蔽日,仅仅一道轮廓便压得人喘不过气。
祂的双目犹如两轮猩红的血月,俯瞰著角斗场內的一切,目光所及,万物皆颤。
角斗场四周,五层环形观眾席如同五道不可逾越的天堑,自下而上,层级分明。
最底层、最外围的第五序列,无数暗影幽魂如沸腾的黑海,它们扭曲翻滚,发出唯有灵魂才能感知的、充满战意与疯狂的无声嘶吼,数量之多,几乎淹没了这一整层。
谭行的目光,却径直落在了第五序列最前排,那唯一一张格外狰狞、由无数利刃虚影构成的“万刃王座”之上。
那代表者第五序列冠军的王座中,一道与他容貌別无二致的虚影,正大马金刀地坐著,一脚甚至踩在王座扶手上,手中一柄虚幻的长刀扛在肩头,下巴微抬,眼神睥睨,那股子仿佛天下地下、唯我独尊的囂张气焰,隔著时空都扑面而来。
“嘖,还是这么能装,看著真特么欠揍!”
他瞥了瞥嘴,隨即视线继续上移。
然而,隨著视线抬高,景象骤然变化。
第四序列的幽魂数量锐减,稀疏了许多,但每一道身影都更为凝实,隱隱透出凶戾的战意。
到了第三序列,幽魂暗影已可称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姿態各异、却皆散发著强大气息的虚影。
他们是被血神选中的战士在角斗场中留下的烙印,是过往荣耀与力量的证明。
第二序列,虚影的数量已变得寥寥,仅有数十之数。
他们沉默矗立,周身缠绕著实质般的煞气或异象,宛如一座座沉默的山岳,仅仅是虚影的目光扫过,都仿佛能撕裂低序列的灵魂。
而最高处,最接近苍穹血神虚影的——
第一序列。
只有六道模糊的身影,沐浴在最浓郁的血色神光中,静静屹立於血神虚影之下。
它们的存在,仿佛本身就是规则。
仅仅矗立,便让下方所有序列死寂无声,如同仰望不可触及的古老传说,永恆而神秘。
五重序列,等级森严。
越往上,位阶越尊,印记越少,也越强大。
这是血神角斗场铁一般的法则,刻在每一寸空间里,也刻在每一个仰望者的魂中。
“呼!”
谭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目光如刀,刺向场中那道逐渐凝实的身影。
“覃玄法,”
他扯了扯嘴角,声音在空旷的角斗场內清晰迴荡:
“又见面了。”
光影彻底稳固,覃玄法的身形完全显现。
他面上原本翻腾的暴怒,竟在看清谭行的瞬间奇异地平息下去,化作一片深潭般的死寂。
只是那双眼底,淤积著化不开的复杂情绪。
“是啊…谭行。”
覃玄法开口,声音沙哑:
“我没想到…真没想到。
破我道心,將我踩下王座,夺走血神注视的……
竟是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我还以为真是那韦正.....”
他顿了顿,一股压抑至极的痛楚与不甘在平淡语调下隱隱沸腾:
“谭行啊,谭行!你断了的,何止是一场胜负。那可是我的成神之路啊!”
“嗤”
谭行笑了,笑声在这肃杀之地显得格外刺耳。
他隨意抬手,食指笔直指向天穹之上那尊笼罩一切的巍峨血影。
“成神?你就是个败犬而已!”
他眉梢挑起,满是毫不掩饰的讥誚:
“看看那位。祂的眼里,何时容得下……”
他目光转回覃玄法,一字一顿:
“败、犬?”
“败……败犬?”
覃玄法眼中锐芒暴涨,忽然放声狂笑,笑声中满是癲狂与孤傲:
“你说我是败犬?
我覃玄法,同辈不败.....十六岁入先天,十八岁凝內罡,二十八岁踏破天人关!纵横天下,你说我是败犬?!”
谭行面无表情,声音平直如铁:
“我在这里打死过你。”
“我二十三岁创立玄法异能高中,將一所平民学堂带入北疆市前三!”
覃玄法向前踏出一步,地面血尘微震,气势升腾。
“我在这里打死过你。”
谭行语调未变,字字凿心。
“我在长城之下,组建玄法称號小队,异域血战,大战中七进七出,名震四方!”
“我在这里打死过你。”
“我连那號称洞彻天地的『感应天王』都敢算计!令他麾下称號小队损兵折將,顏面扫地,我……”
“我在这里打死过你。”
覃玄法鬚髮皆张,周身气势轰然爆发,搅动角斗场血色尘埃:
“如今我已铸就武道真丹!天王不现世,谁敢言必胜我?!”
谭行终於掀起眼皮,看向他,吐字清晰如冰珠坠地:
“我。在这里。打死过你。”
“你……!”
覃玄法气息骤乱,面容肌肉抽搐:
“小杂种.....无相荒漠中,我连『諦听』小队都能玩弄於股掌!
借黄狂的武骨神通,找到无相之神遗留的『门』!布局整整十余年,只待接引神……”
“我、在、这、里、打、死、过、你。”
谭行打断他,这次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一记耳光,狠狠摑在覃玄法那用毕生心血与费劲心机垒起的丰碑上。
覃玄法所有声音戛然而止。
他张著嘴,周身翻腾的气势忽然僵住,隨即剧烈颤抖起来。
那並非恐惧,是愤怒.....
一种前所未有的、几乎要烧穿理智的暴怒。
他覃玄法一生精於算计,喜怒不形於色,自认城府如渊,以天地为棋局。
可眼前这个少年,就用那副油盐不进、不阴不阳的腔调,將他视若生命的骄傲、耗尽心血织就的谋略、血肉拼杀换来的辉煌……轻飘飘地,贬作尘埃。
他感到双耳嗡鸣,脸颊滚烫似火,一股陌生而灼烈的羞耻与狂怒直衝天灵,烧得他眼前发红.....
这辈子第一次,他如此清晰地体味到,什么叫“红温”。
角斗场上空,那两轮悬掛的猩红血月,似乎几不可察地、微微转动了一瞬。
漠然的视线垂落,如同在观赏一场……早在翻开扉页时,便已写好终局的旧戏。
而戏台上的覃玄法,正立在沸腾与崩断的弦上,摇摇欲坠。
覃玄法胸膛剧烈起伏,猛地深吸一口气,將那几乎喷薄而出的暴怒死死压回眼底。
他强行挺直脊背,让声音恢復平稳,强撑著最后一丝体面:
“战吧。”
他盯著谭行,字句从牙缝间碾出:
“这场荣耀试炼,你我皆以性命作注。
规则之下,不死不休。
血神冕下亲定的铁律——被挑战者,需將力量压制至与挑战者同境,以示绝对公平……”
他话音微顿,眼底掠过一丝压不住的孤高:
“这规则,我自然遵守。不过谭行……”
他周身气息开始急速沉降、收敛,从浩瀚的真丹之境一路跌落,最终稳固在內罡层次的波动上。
一股精纯凝练、远超寻常內罡的威势瀰漫开来。
“同境之內,”
覃玄法缓缓抬起手,五指虚握,一柄长枪陡然出现,他缓缓握住,仿佛握住曾属於他的无敌信念:
“我覃玄法,从未败过。”
谭行闻言,咧开嘴,笑了。
那笑容里只有一种近乎狂野的兴奋与期待。
他单手抬起血浮屠,刃尖遥指对方,一字一句,砸在角斗场死寂的空气里:
“呵。”
“同境无敌?”
他歪了歪头,眼神亮得慑人:
“巧了。”
“老子打遍同境.....”
血浮屠微微震颤,发出低沉嗡鸣,仿佛渴饮的凶兽。
“也是,见谁砍谁。”
谭行话音落下的剎那,角斗场中央的空气骤然凝固,隨即被两道同时爆发的身影悍然撕碎!
“轰——!”
覃玄法手中那杆通体暗沉、名为“无间”的长枪,率先刺破寂静。
枪尖震颤,竟无半点破风声,唯有极致的“快”与“毒”,如同潜伏已久的幽冥毒蛇,直噬谭行咽喉!
枪身之上,白色的“无相邪力”吞吐不定,所过之处,连血色光线都仿佛被侵蚀、扭曲。
这一枪,毫无试探,便是绝杀!
凝聚著覃玄法毕生枪术精华与此刻焚心的怒火。
面对这刁钻致命的一枪,谭行不退反进!
他脚下猛然一踏,地面血尘炸开,身形如炮弹般前冲。
手中血浮屠发出一声兴奋的嗜血颤鸣,漆黑的刀身毫无花哨地由下至上,斜撩而起!
刀锋之上,並非寻常罡气,而是浮现出一层深沉如渊、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的灰白色罡芒——归墟神罡!
刀枪瞬间碰撞!
“鐺——!!!”
刺耳的金铁交击声混合著能量爆鸣,炸开一圈肉眼可见的灰黑波纹!
无相邪力与归墟神罡激烈对耗,发出令人牙酸的“滋滋”声响。
覃玄法眼神一凝。
枪尖传来的触感无比沉重、凝实,更有一股诡异的吞噬消解之力,竟在迅速侵蚀他附著的邪力!这绝非普通內罡!
“有点门道!”
覃玄法心中凛然,面上却冷哼出声,枪势应声陡变!
无间长枪於其手中,真如通灵之蛇,枪身一抖、一颤,霎时间幻化出七道凝实无比的灰白枪影!
这七道枪影並非虚招,竟暗合北斗天璇星位,彼此气机勾连,封锁上下四方,森然刺向谭行周身七大生死要穴!
枪影未至,那股专破罡气、腐蚀筋骨血肉的阴寒邪力已穿透空气,带来刺骨寒意。
这正是他当年在北斗学府位列“天璇序列”时,得以修习的顶级真武功法——天璇七杀枪!枪出七杀,绝灭生机!
面对这笼罩而来的绝杀枪网,谭行眼中非但无惧,反而爆发出更炽烈的战意。
“北斗学府天璇序列的招牌枪法?拿来唬你爹?”
他狂笑一声,竟不守反攻!
体內归墟神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涌,透过双臂灌注於血浮屠之中。
那暗沉刀身猛地一震,仿佛甦醒的凶兽,发出低沉咆哮。
血浮屠在他手中却仿佛活了过来。
刀光如匹练,又似泼墨,没有固定章法,只有最直接、最暴力的劈、砍、斩!
每一刀都势大力沉,裹挟著归墟神罡那吞噬一切的霸道特性,以力破巧,悍然撞向那七道枪影!
鏘!鏘!鏘!鏘!
碰撞声连成一片急雨!
灰白邪力与暗沉罡气不断炸裂,在两人之间形成一片能量乱流。
谭行的刀法看似粗野,却总能在间不容髮之际精准斩中最具威胁的枪影本体,归墟神罡更是隱隱克制著无相邪力的侵蚀特性,甚至反噬!
覃玄法越打越是心惊。
他自负同境无敌,枪法、经验、邪力皆臻化境,可对面这小子的罡气实在诡异,力量也大得不像话,战斗本能更是野兽般敏锐。
自己精妙的枪招竟被对方用这种蛮横的方式不断化解、压制!
覃玄法眼底狠色一闪!
“无相·千幻!”
他猛地暴喝,周身无相邪力轰然沸腾,身形似乎模糊了一瞬。
下一剎那,竟有足足三道凝实的“覃玄法”持枪刺出,从三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袭向谭行!气息、邪力、杀意完全一致,难辨真假!
这已是近乎武骨神通的幻杀之术!
面对这绝险杀招,谭行眼中嗜血的光芒却大盛!
“来得好!”
他不闪不避,甚至闭上了眼睛!
全身归墟神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並非向外扩散,而是向內塌缩,凝聚於血浮屠刀锋之上!
一股仿佛万物终结、归於虚无的可怕意境,自他刀尖瀰漫开来。
就在三道枪尖及体的前一瞬——
谭行睁眼,挥刀。
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深邃到极致、仿佛连目光都能吸走的暗弧,悄无声息地划过一个半圆。
斩道·寂灭!
嗤——!
如同热刀切入牛油。
那三道气势汹汹的幻身枪影,连同其中蕴含的澎湃无相邪力,在接触到这暗弧的瞬间,便无声无息地消散了。
不是击溃,而是如同被投入了无底深渊,彻底湮灭,归於虚无!
“什么?!”
覃玄法真身巨震,绝招被破带来的反噬让他气血翻腾,脸上终於露出骇然。
这到底是什么罡气?!
破开千幻的暗弧刀芒去势未绝,已然临身!
覃玄法仓促间横枪格挡,將无间长枪催动到极致,灰白邪力如潮涌出。
“鐺——轰!!!”
比之前猛烈十倍的爆炸响起!
覃玄法只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力与吞噬感传来,虎口崩裂,他整个人如遭雷击,向后倒飞出去,双脚在角斗场地面上犁出两道深深的沟壑!
尚未站稳,一股恶风已然扑面!
谭行根本不给丝毫喘息之机,人隨刀走,如影隨形!
血浮屠带著撕裂一切的煞气,再次当头斩落!刀身上的归墟神罡越发浓郁深邃。
“哼!”
覃玄法一声冷哼,嘴角溢血,眼中再无半分从容:
“无相神力——燃!”
他周身原本汹涌的灰白邪力,此刻竟然剧烈翻滚,近乎燃烧起来,手中无间长枪发出悽厉尖啸,枪身浮现无数扭曲邪纹,一枪刺出,邪力凝成一道惨白的螺旋尖锥,所过之处空间都微微波动!
这是搏命一击!
谭行狂吼,兴奋到颤抖,归墟神罡毫无保留地灌注进血浮屠,刀身嗡鸣变得高亢尖锐,仿佛深渊巨兽的咆哮。
他不闪不避,迎著那惨白螺旋尖锥,斩出了至今最强的一刀!
刀光与枪锥,如同宿命般再次对撞。
这一次,没有巨响。
只有一声沉闷的、仿佛什么东西被咬碎的怪异声响。
惨白螺旋尖锥,在触碰到那极致的暗黑刀芒时,如同冰雪遇沸油,迅速消融、塌缩!
归墟神罡,吞噬万气,归於虚无!
“!!!”
覃玄法目眥欲裂,眼睁睁看著自己的全力一击被无情吞噬,那恐怖的黑色刀芒在湮灭枪锥后,余势不减,在他瞳孔中急速放大!
噗嗤!
血光迸现。
一条握著无间长枪的手臂,冲天飞起。
覃玄法惨叫著踉蹌后退,右肩处鲜血狂喷,断臂之痛让他英俊的脸庞彻底扭曲。
谭行单手持刀,血浮屠的刀尖斜斜点地。
归墟神罡如活物般在暗沉的刀身上缓缓流淌,仿佛一层吞噬光线的灰白色水银。
他胸膛微微起伏,呼吸带著战斗后的灼热,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如同黑夜中燃烧的炭火,死死锁定在面如死灰的覃玄法身上。
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因激烈搏杀而有些乾涩的嘴唇,勾起一个混合著嘲讽与狂意的笑容:
“同境无敌?”
声音清晰地在死寂的角斗场中迴荡。
“就凭你?”
谭行抬脚,一步步向失去手臂、狼狈不堪的覃玄法走去.....
“说实话,老子都没用全力,血神爸爸的赐福都还没用上……”
他在覃玄法身前数步处站定,居高临下地俯视著这位曾经的“天璇序列”天才、玄法高中的创立者、自詡同境不败的武道真丹。
一字一句,如同冰锥,凿进对方濒临崩溃的心里:
“你,就这副德行了?”
“你、真、的、太、垃、圾、了。”
“……”
覃玄法仿佛没有听见这诛心之言。
他直勾勾地盯著地上那条断臂——那只曾握笔制定《玄法校规》、曾持枪在长城外杀出“玄法诡枪”凶名、曾在无数个凌晨颤抖著举起又放下的右手。
此刻,它像块被扔掉的腐肉,蜷在血污里,指尖甚至还在微微抽搐。
野心、算计、傲慢……都隨著断口处汩汩外涌的鲜血,迅速变冷、变僵。
而一种被他用三十余年算计与狠厉死死镇压在灵魂最深处的情绪,却如同挣脱牢笼的恶鬼,顺著冰冷与虚弱的缝隙,猛地攫住了他的心臟。
自卑。
这个他这辈子最不敢面对、最羞於承认的情绪,此刻却像淬毒的匕首,再次捅穿他所有偽装。
他抬起猩红涣散的眼,望向对面提刀而立的少年。
恍惚间,谭行的身影竟与另一个灼烧他半生的梦魘缓缓重叠——
马甲雄!
那个名字,像烧红的烙铁,又一次烫在他苦心维持的尊严上。
他甚至又记起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时的他从北疆荒僻的乡村走出,身负“万道枪骨”,被称作“北原道的希望”。
他意气风发来到天启参加联邦武道模擬考,他以为能再次靠一双拳头、一桿铁枪,靠著他的一身武道天赋,就能打穿天启,名震联邦。
直到大赛上,他遇见了那个男人。
烈阳世家嫡子,烈阳天王长子——马甲雄。
三刀。
仅仅三刀。
他苦练十六年的枪势、被乡里誉为“百年奇才”的骄傲、对未来的全部狂想,被劈得粉碎。
那之后,高中、大学、长城巡游……他拼了命地修炼,榨乾每一滴潜力,却只能一次次仰望那道如正午烈日般刺眼的背影。
只要站在马甲雄身边,他就像条瘸了腿的野狗,连不甘都显得可笑。
最痛的不是输。
是对方根本没把他当成“对手”。
大学毕业那年,北斗,星海,战爭三大学院內部交流赛。
他代表北斗学府“天璇序列”出战,再一次——被他轻而易举地击溃。
赛后,马甲雄甚至走过来,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依旧是那温朗如朝阳的该死笑容:
“玄法,实力进步很大啊。”
那一刻,他听见自己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
他不需要同情,更不要这种居高临下的“夸奖”。
他不需要同情,更憎恶这种居高临下的“认可”。
他从北疆那片外围冻土爬出来——那是连野狗都会饿死啃尸的荒村。
他吞过脏雪,嚼过草根,咽下硌喉的糠菜,在无数个冻透骨髓的寒夜里,握著那杆磨破掌心、浸透鲜血的铁枪,走到现在……
不是为了做谁辉煌人生的註脚!
他要的是功成名就,是人前显圣,是把“覃玄法”三个字烙进联邦史诗!
让当年所有斜眼看他、施捨他、背后嘲笑他的人,余生只能跪著仰望!
直到那一天。
他眼前浮现了那一线幽暗的“希望”。
那个名为【人前显圣】的系统,散发著邪神低语般的蛊惑。
他知道那是污染,是灵魂的毒药。
那又如何?
它给了他从泥潭里爬出来的第一根绳子,给了他將马甲雄那张永远从容的笑脸撕碎的力量!
他用了多少年?流了多少血?算计了多少人?
终於,他將那个如日中天的烈阳之子,设计坑杀在冥海深处的“碎骨海岸”。
那时,他隱匿在战场最外围的阴影里,听著骸骨魔族那两尊泰坦巨物震彻海域的嘶吼,看著马甲雄的烈阳罡气如脆玻璃般迸裂,被生生撕碎吞噬,栽进无尽冥海!
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终於把那份该死的自卑碾成了粉,踩进了泥。
他以为自己早就忘了,早就贏了。
可现在……
就因为这个不知从哪个阴沟里钻出来的野小子,用最蛮横、最不讲道理的方式,將他半生心血搭建的一切——名声、力量、未来——砸得粉碎。
隨意的....就像很多年前,村里那个村长家的胖小子,隨手打翻他熬了三天短工才换来的一碗热肉羹。
汤水混著冻土,他那点可怜的尊严,在围观者的鬨笑中滋滋作响。
那种无论怎么挣扎、如何拼命,在真正的“天之骄子”面前,永远低人一等、不值一提的……卑微,又回来了。
甚至更狠,更痛。
因为这次,他连欺骗自己的藉口都没有。
他確確实实,在同境之下,被对方以最碾压的姿態击溃,夺走一切。
覃玄法僵在原地,任由鲜血浸透半身,忘了疼,忘了恨,甚至忘了愤怒。
眼底最后那点支撑著他的孤高与癲狂,正被这冰潮般涌回的自卑,一寸寸吞噬、淹没。
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缩在人群最角落,看著马甲雄沐浴万丈荣光,只能把拳头攥得指甲陷进肉里,却连一声都不敢吭的……荒村少年。
只是这一次,再没有三十年给他去爬了。
也没有另一个“系统”,能递给他从头再来的“希望”。
角斗场上空,血神那对猩红巨眸寂静垂落,將这一幕尽收眼底。
那永恆的血色中,仿佛闪过一丝对人类脆弱情感的不愉审视。
但就在覃玄法眼神涣散、心神彻底失守的剎那——
“妈的!”
谭行一声暴喝,身形已如黑色闪电般撕裂两人之间的距离!
他根本懒得琢磨对手为何失神,只觉得胸中一股无名火起....
战斗之中,敢在他面前走神?这是看不起老子?!
血浮屠发出兴奋的低鸣,归墟神罡在刀锋上沸腾成灰白色的火焰,没有任何花哨,只有最纯粹、最暴力的——竖劈!
刀锋撕开空气的尖啸,终於將覃玄法从绝望的深渊中猛然拽回!
他瞳孔骤缩,死亡的寒意瞬间压倒了所有溃散的情绪。
求生的本能驱使他仅剩的左臂仓促格挡,残存的邪力疯狂涌出——
“鐺——!!!”
刀臂相交,竟发出金铁撞击般的闷响!覃玄法左臂衣袖瞬间炸裂,露出下面紧贴皮肤、瞬间激活的无相邪能。
但仓促之间的防御,怎能抵得住谭行蓄势已久的全力一刀?
“咔嚓!”
那邪能护甲只坚持了一瞬,便裂纹蔓延!
覃玄法整个人如被劈得倒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左臂传来骨骼碎裂的剧痛,重重砸在数十米外的角斗场壁垒上,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
“嗬……嗬……”他顺著墙壁滑落,单膝跪地,又是一口鲜血呕出,眼前阵阵发黑。
谭行提刀缓步走来,他歪了歪头,看著狼狈不堪的覃玄法,语气里满是不耐与戾气:
“打不过就开始做梦?”
“老子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
他举起血浮屠,刀尖遥指对方咽喉:
“输了,还他妈摆出一副要死要活德行的废物。”
角斗场上空,血神的眸光微微流转,那丝不愉似乎悄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声嘉许。
战斗,从来不需要多余的怜悯与感怀。
唯有胜者,方有资格站立。
“哈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跪倒在地的覃玄法忽然笑了起来。
那笑声起初低哑,隨即越来越响,越来越癲狂,最终化作一阵撕裂喉咙般的歇斯底里的狂笑!
他英俊的脸庞此刻扭曲如从地狱爬出的恶鬼,两行粘稠的、混杂著血丝与某种灰败能量的血泪,从眼角缓缓淌下,在脸颊上犁出触目惊心的痕跡。
他猛地抬起头,血泪滑过下頜滴落,那双原本已近死寂的眼睛,此刻却亮得骇人——里面翻涌著疯狂、不甘、释然,以及某种斩断一切的最后决绝。
“你贏了……你贏了!”
他嘶声笑著,每个字都像从肺里咳出来:
“作为『人』的覃玄法……输了!输得连最后一点尊严都不剩!罢了……罢了!!”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断臂处鲜血仍在涌出,气势却诡异地攀升,那是一种拋弃了一切枷锁、坠入深渊前的最后燃烧:
“可我覃玄法这一生....”
他嘶吼著,声音穿透角斗场的死寂,仿佛要將毕生的压抑全部喷发:
“也算他妈的轰轰烈烈过!联邦五道,谁没听过『玄法诡枪』的名號?!谁没听过我覃玄法的大名?!谁?!”
悲壮与疯狂在他的嘶吼中纠缠炸裂。
“大丈夫生於天地间....”
他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那即將吞噬他的无尽邪力,脸上浮现出一种扭曲而炽烈的光芒:
“不能九鼎食……那便——九、鼎、烹!”
“轰——!!!”
话音砸地的剎那,他周身原本萎靡的无相邪力,如同被点燃的油海,彻底暴走!
“呃啊啊啊——!!”
非人的痛苦咆哮从他喉咙深处炸开!右肩断口处的血肉疯狂蠕动、膨胀、撕裂!
一条完全由灰白骨质构成、缠绕著蠕动邪异纹理、指尖滴落著腐蚀粘液的狰狞怪手,猛然破体而出,五指如鉤,骨节反张,散发出纯粹的不祥与恶意!
他的躯体开始不自然地畸变、膨胀!
肌肉賁张隆起,將残破的衣物撑成碎片,皮肤之下仿佛有无数活物在窜动、重组,灰白色的邪力纹路如同有生命的藤蔓,爬满他急剧异化的体表!
最骇人的变化发生於面部——脸颊血肉自两侧撕裂,四只惨白、无瞳、只余一片混沌灰白的邪眼,依次挣开束缚,在他脸上森然睁开!
六只邪眼.....
连同原本那双属於“覃玄法”的、此刻正缓缓闭合的人类眼睛.....
同时存在於此畸变的头颅之上,冰冷地、死死地锁定了前方的谭行。
覃玄法缓缓闭上了……那最后一双属於“人类”的眼睛。
最后的人性如风中残烛,摇曳將熄。
而无尽的记忆碎片,化作决堤的洪流,將他吞没....
七岁,北疆,冻土荒村,那个雪能埋骨的冬天。
他蜷在漏风的窝棚角落,看著母亲颤抖著手,將最后半块掺著麩皮的糠饼掰成三份。
两份塞给炕上气若游丝的父亲,一份,留给他。
她转身去挖冻结的草根时,他看见她后颈龟裂的皮肤,渗出的血珠凝成暗红色的冰渣。
那夜,父亲再没醒来。
母亲用冻僵的手,怎么也合不上父亲那双望著破屋顶的、空洞的眼睛。
她把他搂进怀里,冰凉的嘴唇贴著他耳朵,哑著声音,一字一顿:
“狗蛋,要活出个人样。”
活出个人样。
六个字,像六根烧红的钉子,从此钉穿了他的魂。
.....
十二岁,村里那间凑出来的“公益学堂”。
村长对满屋冻得瑟瑟发抖、手脚生冻疮的少年们说:
“你们当中,要是有人能觉醒异能,或者有武道天赋,考上北疆市里的中学……那就真是,鲤鱼跃龙门了。”
他低头看著自己生满冻疮却异常稳定的手,第一次隱约感觉到,掌心握住那根削尖的木棍时,体內有什么东西在微微发烫。
那天放学,村长家的儿子带著一群孩童抢了他辛苦砍的柴禾,把他推倒在结冰的泥坑里。
他趴在冰冷刺骨的泥水中,听著那些远去的、属於“正常孩子”的嬉笑,没哭。
只是把十指狠狠抠进冻土,指甲翻裂,混著泥土与血。
龙门……他要跃过去。
把这座生来就压在他头顶的、名为“出身”的大山,连同那些嘲笑,统统碾碎!
.......
十六岁,北原道少年武道大比决赛场。
他一桿铁枪挑翻所有对手,被观礼的北斗学府特使当场点中。
“万道枪骨!十年难遇!”
满场欢呼如潮,陌生的镁光灯刺得他眼睛发酸。
他接过那尊冰冷沉重的奖盃时,手在微微颤抖。
视线穿过晃眼的光,他看见人群最外围,母亲挤在那里,穿著那身洗得发白、袖口磨破的旧袄,远远地望著他。
她一边笑,一边不停地用袖子擦眼睛。
那天夜里,他对著奖盃坐了一宿。
人样……他好像,快要摸到了....
.....
十八岁,天启市,联邦武道模擬考,中央擂台。
镁光灯匯聚如昼,观眾的声浪像潮水般拍打著擂台边缘。
他紧了紧手中那杆陪伴多年的铁枪,深吸一口气,踏上光洁的合金地板。
然后,他看到了对面那个身影。
马甲雄。
那个少年甚至没有特意摆出架势,只是隨意地站在那里,一身绣著烈阳纹路的战袍纤尘不染。
他周身仿佛自然流转著一层无形的光晕,从容,平静,与生俱来的贵气与强大,如同呼吸般自然散发。
那一刻,覃玄法的心臟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
不是恐惧。
是一种更尖锐、更灼烫的东西——自卑,羡慕,乃至嚮往。
马甲雄,活成了他梦想中“人样”的极致:
天赋、家世、荣耀、万眾瞩目……
一切他都匱乏的东西,对方似乎生来就拥有。
那不仅仅是对手,那几乎是他贫瘠想像所能勾勒出的、关於“成功”与“强大”最具体的幻影。
他不得不承认...
哪怕这承认像刀割一样疼....
马甲雄,就是他曾幻想自己有一天能成为的样子。
裁判的哨声刺耳响起。
没有试探,他將心中翻涌的复杂情绪全部压进枪尖,一出手便是苦练万遍、凝聚了全部骄傲与期盼的杀招!
枪影如龙,撕裂空气,带著他十二年的汗水、北原道的希望、以及那股想要证明“我也能站在光里”的狠劲,咆哮著刺向那道耀眼的身影。
然后....
他看到了光。
那不是形容,是真实的、灼目的、仿佛能焚尽一切阴霾与尘埃的烈阳光芒,从马甲雄手中的刀锋上迸发!
第一刀。
煌煌刀光如大日初升,堂堂正正,碾压而来。
他的枪势,他引以为傲的“万道枪骨”催发的內气,像遇到骄阳的薄雪,瞬间消融。
巨力传来,他虎口崩裂,铁枪发出哀鸣,整个人踉蹌后退。
第二刀。
刀光再起,更快,更烈!如日中天,无可躲避。
他拼尽全力格挡,枪桿弯曲成一个惊心动魄的弧度。
骨骼发出咯咯响声,五臟六腑仿佛都被震得移位。鲜血从嘴角溢出,视野开始晃动。
那光芒刺得他睁不开眼,也刺穿了他所有技巧与侥倖。
第三刀。
这一刀,仿佛夕阳沉落前最炽烈的一瞬,带著终结的意味。
他看到了,却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反应。
身体跟不上意识,力量早已溃散。
刀光临体,没有疼痛,只有一种彻底的、冰冷的虚无感。
“鐺啷!”
铁枪脱手飞出,在空中旋转著,划出无力的弧线,重重砸在擂台边缘。
他僵立了一瞬,隨即膝盖一软,重重跪倒在地,又无力地向前扑倒。
视野贴著冰冷的地板,他能看见自己颤抖的手指,和不远处那杆静静躺著的铁枪。
裁判的读秒声遥远得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二、一!比赛结束!胜者,天启第一高中,马甲雄!”
潮水般的欢呼瞬间將他淹没,但那些声音都模糊了。
他耳朵里只剩下自己血液冲刷鼓膜的轰鸣,嗡嗡作响。
还有看台上,一些並未刻意压低、却清晰钻进他灵魂的议论:
“嘖,还以为『万道枪骨』多厉害,原来就这三下?”
“乡下地方出来的,没见过真场面,底子太虚了。”
“和马甲雄比?不是一个层次的……”
他躺在那里,望著体育馆穹顶刺眼到令人晕眩的白炽灯阵列。
那光芒,和刚才將他吞噬的刀光,一样冰冷,一样遥远。
原来他苦练十二年引以为傲的一切,他以为摸到了边的“人样”,在那个真正站在光中的人面前,脆薄如纸,一触即溃。
那天夜里,他没有去找带队老师,也没有回驻地。
一个人走进天启市迷宫般的霓虹街巷,漫无目的地走著。
直到暴雨毫无徵兆地倾盆而下,將他彻底浇透。
冰凉的雨水顺著头皮流淌,浸湿了那件为了这次大赛,咬牙买下的、他当时觉得最能衬出自己“不凡”的崭新战袍。
雨水混著额角不知何时磕破流下的血,淌进嘴里,一片咸涩。
他抬起头,任由雨水冲刷著脸。
眼前晃动的,依旧是那三道斩落他所有骄妄的、如大日般的刀光,以及马甲雄收刀归鞘时,那平静的、甚至未曾多看他一眼的侧影。
那身影,如此耀眼。
也如此,遥不可及。
....
二十三岁,玄法异能高中,校长室。
他签下最后一份艰难爭取来的拨款文件,推开窗。
夕阳正浓,橘红色的光泼洒在操场上。那些穿著洗得发白的统一运动服,眼神却亮得灼人的学生们正在奔跑、对练、咬著牙举起远超体重的槓铃。
汗水在夕阳下闪著光,呼喝声充满了粗糙的生命力。
这所他从几乎为零的预算、错综的人际网络和政策夹缝中,一点一点撕扯、堆积、重塑起来的平民学校,歷经五年,终於被官方榜单承认,挤进了北疆市前三。
年轻的秘书抱著一摞文件站在门口,看著窗外景象,眼眶难以抑制地红了,声音带著哽咽:
“校长,我们……我们真的做到了!”
他转过身,点了点头,脸上甚至配合地露出一丝应有的、淡淡的欣慰。
“嗯,做得很好。”
然后,他再次望向窗外,望向那片被夕阳镀上金边的、充满希望的喧腾。
心中,却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冰冷的空洞。
做到了?
不。
这算什么“做到”?
北疆第三?在这远离联邦核心的边城称王?
这和他蜷在冻土荒村时仰望的“龙门”,和他被马甲雄三刀劈碎时渴望的“认可”,和他耗尽心血想要涂抹掉的“卑微”,相差何止万里!
他要的,从来不是这种偏安一隅的“成功”。
他要的是天启!是当年模擬考赛场上,那些从世家包厢、从贵宾席、从无数双傲慢眼睛里投来的轻蔑目光,有一天不得不生生扭转,变成惊愕、忌惮,乃至恐惧!
他要的是“烈阳”、“统武”、“霸拳”、“镇岳”....这些姓氏背后的庞然大物,有一天在议会、在战场、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任何场合,都不得不停顿、审视,然后说出他的名字....
“覃、玄、法!”
他要的,是把自己这个从泥土和鲜血里爬出来的名字,不是刻在什么边城榜单上,而是用最滚烫的方式,烙进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最深的骨血里!
窗外的欢呼与汗水,此刻只让他感到一种隔膜的喧囂。
这条路,才刚起步,而他已嫌太慢。
.....
二十六岁,无相荒漠深处。
邪能卷著砂砾,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
黄狂——那个觉醒了“天闻武骨”、能聆听万物细微波动、心思却直率得像荒漠狂风一样的汉子,也是他最重要的兄弟,抹了把脸上的沙尘,咧开乾裂的嘴唇,撞了下他的肩膀。
“老覃,放心!等这次找到那扇『门』,把坐標报上去,军功绝对够咱俩都换个『特级战斗英雄』!光宗耀祖。
他当时也笑了,抬手拍了拍黄狂结实的、肌肉虬结的后背,力度恰到好处。
“嗯,风光。”
声音平稳,毫无波澜。
可他心里清楚,从踏入荒漠、从【人前显圣】系统低语著將“门”的线索“巧合”般推到他眼前时,黄狂和他的武骨,就只是一把註定要用来叩门、然后折断的“钥匙”。
他记得那是新月无光的深夜,流沙之下庞大的遗蹟终於显现。
黄狂根据他“无意”透露的线索,激发武骨神通“諦听之眼”,浑身毛孔都在渗血,终於感应並定位到了“门”那虚无縹緲的时空锚点。
那一刻,黄狂疲惫却兴奋地回头,染血的脸上笑容灿烂如孩童:
“老覃!找到了!我真的找……”
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自己的手,已经穿透了他的后心。
那只手上缠绕著提前绘製好的、抑制再生与灵魂波动的无相邪符。
没有激烈的搏杀,只有最冷静、最精准的背叛。
他亲眼看著黄狂眼中的光芒从狂喜到惊愕,再到难以置信的茫然与破碎,最后定格为一片死寂的灰败。
直到身躯缓缓软倒,那双眼睛依旧圆睁著,倒映著自己那副冰冷到极致、甚至没有丝毫波澜的面孔。
他利用黄狂的武骨余韵作为祭品与坐標,启动了早已布置好的邪仪。
当那扇仿佛由无数扭曲知识与低语构成的“无相之门”在虚空中洞开一线时,磅礴的邪力与知识洪流冲刷著他的灵魂,也彻底淹没了所有身为为『人』的所有退路。
那一刻,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灵魂深处某个柔软的、属於“人”的部分,隨著黄狂眼中最后一点光的熄灭,发出了细微的、咔嚓的碎裂声,然后彻底沉寂,死去。
取而代之涌入的,是澎湃强大到令他战慄的力量,以及隨之而来的、更彻底、更绝对的……冰冷与空洞。
他踏著兄弟尚未冷透的脊樑与信任,向上攀爬。
离“人”的岸边,更远了一步。
离深渊的怀抱,更近了一分。
......
三十岁,冥海深处,碎骨海岸。
这里没有光,只有永恆咆哮的黑色怒涛,以及瀰漫在空气中、浓得化不开的血腥与死亡气息。
他潜伏在战场最混乱、最边缘的阴影褶皱里。
目光,穿透层层能量乱流与廝杀的身影,死死锁定在那片最炽烈的战团中心。
马甲雄。
即使在这地狱般的战场上,他依旧如同一轮坠入冥海的烈日,烈阳罡气辉煌璀璨,挥刀间净化大片骸骨魔族。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不是同龄的天才,而是骸骨魔族真正的高阶战爭巨兽——两尊如同移动山岳的骸骨泰坦。
战斗惨烈到无法形容。罡气与死灵能量的对撞让战场都在颤抖、碎裂。
他耐心地等待著,等待著系统计算中那“唯一”的可能。
终於!
一尊泰坦付出了半片身躯崩碎的代价,以近乎同归於尽的姿態,用残留的巨爪悍然撕开了那固若金汤的烈阳罡气领域!另一尊泰坦的毁灭吐息,几乎同时淹没其中!
辉煌的烈阳,在这一刻出现了致命的黯淡与裂隙。
他看到了马甲雄脸上闪过的不甘,听到了那声被冥海怒涛几乎淹没的怒吼,看到了那曾经將他骄傲碾碎的三刀绝技,在泰坦的骸骨上迸发出最后、也是最灿烂的光华……
然后,光灭了。
如同被巨浪扑灭的火把。
连同那具承载了无数荣耀与期待的身躯,一同被冥海无尽的黑暗与骸骨碎渣,彻底吞噬、湮没,再无痕跡。
压在他心头十几年,如同梦魘、如同標尺、如同他渴望成为却又憎恶无比的幻影……消失了。
预想中排山倒海的狂喜没有到来。
没有激动,没有颤抖,没有哪怕一丝的快意。
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死寂的、令人灵魂都感到寒冷的平静,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虚无。
那个在雪夜窝棚里,对著母亲发誓要“活出个人样”,並为此燃烧了三十年的北疆少年,仿佛也隨著冥海那道熄灭的烈阳光芒,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海底,再也不见。
他低下头,摊开自己的手掌。
掌心一缕如同活物般缓缓蠕动、盘旋的灰白色邪力纹路。
它冰冷、强大、充满诱惑,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血肉与灵魂深处。
这是【人前显圣】系统给予的最终“馈赠”。
也是他投向无相之神,再也无法剥离的……永恆烙印。
.....
而现在……血神角斗场。
断臂处传来的不再是剧痛,而是灼热的麻木,仿佛有什么正从伤口、从骨髓深处甦醒、增殖,要將他从內到外彻底替换。
他能感觉到,源自无相之神的冰冷力量,正贪婪地吞噬他最后的人性,狂热地重组他的血肉、骨骼与灵魂。
真是讽刺啊……
他这一生,像条疯狗一样撕咬、攀爬、算计。
他燃烧了童年、烧尽了温情、烧毁了底线,所为的,不过是抹去骨血里与生俱来的卑微,证明自己配得上母亲口中那个“人样”,能堂堂正正站在光里,被世人看见,被时代认可,被歷史铭记——人前显圣,光耀门楣!
可这一路,他踩碎了什么?
是父亲临终前望著破屋顶时,那未能说出口的期盼?
是母亲用冻裂的手搂著他,嘶哑叮嘱“要活出个人样”时,眼中那点微弱的希冀?
还是……兄弟黄狂毫无保留递过来的后背,与那声戛然而止的“老覃”?
抑或是那个曾如烈日般耀眼、让他憎恨又暗自嚮往的对手——马甲雄,最后崩碎於冥海的烈阳与骄傲?
他得到了他能算计的一切。
可最终,能让他继续“存在”、竟是彻底拋弃为之奋斗一生的“为人”资格,將这副沾满至亲期望、兄弟热血与对手亡魂的躯壳与灵魂,当作祭品,完整地献祭给无底的深渊。
记忆的碎片在邪力焚烧的烈焰中扭曲、变形、最终融化成混沌的背景杂音。
母亲冻裂的后颈,父亲闔不上的眼,泥坑里的冰水,奖盃的冰冷,黄狂倒下时茫然的瞳孔,马甲雄崩碎的烈阳,冥海的黑浪……还有此刻,角斗场穹顶上,血神那对漠然俯视的猩红巨眸。
原来这一路挣扎攀爬,他不过是从一个名为“贫困”的深渊,爬向一个名为“自卑”的深渊,再坠入如今这个名为“执念”与“墮落”的……无底深渊。
所谓野心,所谓算计,所谓不择手段的向上攀爬,所谓不择手段的人前显圣....
自始至终,都只是那个很多年前、在北疆冻土寒风中簌簌发抖的自卑少年,对著冰层倒影中那个永远不够强壮、永远不够优秀、永远低人一等的自己,发动的一场持续了一生、耗尽灵魂的……漫长战爭。
而现在。
这场持续了一生的战爭,终於要迎来它的终局了。
胜者將获得扭曲的新生。
败者……將支付最终的代价:他身而为人的一切。
“人生漫漫……”
他最后那片尚未被邪力侵蚀的、属於“人类”的嘴唇,极其轻微地嚅动了一下,吐出几个几乎听不见的气音。
那声音里,没有恨,没有怒,只有一丝深入骨髓的疲惫,和一点尘埃落定般的、近乎解脱的嘲弄。
“那就……这样吧。”
“吼——!!!”
覃玄法....不,那具已完成最终畸变、身高超过三米、浑身覆盖灰白骨甲与蠕动邪纹、生有六只邪眼的可怖怪物——猛地睁开所有眼睛!
属於“覃玄法”的所有温情、挣扎、不甘、野心与执念,在六只邪眼同时睁开的剎那,被无相之力彻底焚化、净化!
只剩下最原始、最纯粹、最暴戾的——对毁灭的渴望,以及对赐予它新生的“主”的,扭曲忠诚。
它(他)朝著前方的谭行,昂起狰狞的头颅,发出一道撕裂灵魂的、混合著无数记忆迴响与纯粹邪能的嘶嚎:
“杀……!!!”
嘶嚎声中,它周身灰白邪力如火山喷发般冲天而起,在其身后隱隱凝聚成一尊模糊不清、充满无尽低语与扭曲知识感的庞大虚影!
无相眷属,第一序列.....
诡语者,於此诞生!
其存在本身,便是由北疆冻土的贫困、成长路上如影隨形的自卑、对力量不择手段的背叛、吞噬灵魂的疯狂野心、以及最终一无所有的彻骨绝望……
共同浇灌催生而出的,一尊畸形、邪恶、却又强大无比的罪恶邪物。
第274章 人生漫漫,那就这样吧...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