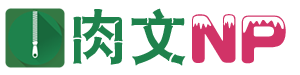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咕咚!”
这声闷响,在这喧囂刚过的中院里,显得格外沉重且滑稽。
隨著第三大碗烈酒像灌下水道一样灌进肚子里,许大茂那原本挺得笔直的腰杆子,瞬间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根钢筋。整个人在太师椅上晃了三晃,两只眼珠子往上一翻,只露出一大片惨白的眼白,那模样,活像是个刚被放了血的瘟鸡。
“我……茂爷我还能喝……傻柱,你丫……別跑……”
许大茂的舌头像是打了结,含糊不清地嘟囔著最后的倔强。话音未落,他身子一软,就像一摊没了骨头的烂泥,“出溜”一下顺著桌子腿滑到了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紧接著,那喉咙里便传出了如同拉风箱一般、断断续续的死猪般的呼嚕声。
三碗不过岗,许大茂这是三碗见阎王。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拼酒现场,瞬间分出了胜负。
傻柱手里端著那个空了的大瓷碗,身子晃得跟风中的枯芦苇似的。他也快不行了,胃里像是有团火在烧,烧得他五臟六腑都疼,喉咙眼儿里直泛酸水。
但他贏了。
他用那只完好的左手,狠狠地抹了一把嘴角的酒渍,那只浑浊的独眼中,闪烁著一种近乎病態的、报復后的快意。他轻蔑地瞥了一眼蜷缩在桌子底下、跟条死狗没两样的许大茂,把碗重重往桌上一顿:
“孙子!跟爷爷斗?你还嫩点!”
傻柱大著舌头,对著桌底下的许大茂啐了一口:
“今儿个是你大喜的日子,爷爷就送你个不举的大礼!喝成这副德行,我看你今晚这洞房怎么入!你就搂著酒瓶子睡吧!”
说完,他在易中海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那背影虽然佝僂,虽然狼狈,却透著一股子復仇后的舒爽和淒凉。
这一场拼酒的大戏落幕,但这流水席的残局,却更让人触目惊心。
原本满桌的大鱼大肉,此刻连个油花都没剩下。
这帮饿了一年多的邻居,那是真的把“光碟行动”贯彻到了极致。別说打包了,那盘子被拿馒头蘸著菜汤擦得鋥光瓦亮,甚至有几个半大小子还不甘心地拿著盘子舔了两口,比刷过的还乾净,都能当镜子照人影了。
阎埠贵手里拿著个空网兜,原本是想趁乱装点剩菜回去的。这会儿他站在桌边,看著那一摞摞比脸还乾净的盘子,直嘬牙花子,那一脸的褶子都挤成了苦瓜,痛心疾首地拍著大腿:
“哎哟喂!这帮败家玩意儿!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啊?咋连口汤都不剩呢?”
阎埠贵心疼得直跺脚,眼镜片都在颤抖:
“我还寻思著带点剩菜回去,晚上给解娣煮麵条,借个肉味儿呢……造孽啊,真是造孽!这可是大油水的席面啊,就这么造没了!”
就在这时,那三个忙活了一中午、累得满头大汗的大厨走了过来。
领头的胖师傅用围裙擦了擦手,看著这一地狼藉,又看了看早已不省人事的主家许大茂,脸上的肥肉抖了抖,一脸的难色。
“哎,这位大爷,您看这……这也没剩啥了。但这工钱……”
胖师傅搓著手,油腻腻的围裙上满是污渍,目光在周围这些剔著牙、打著饱嗝却没人掏钱的邻居身上扫来扫去。
“主家喝成这样了,这钱谁给结一下?”
这一问,周围原本还热热闹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不少。
阎埠贵一看提到钱,那反应比兔子还快,立马缩了脖子,假装在那收拾板凳,嘴里哼哼唧唧的,仿佛突然耳聋了一样。
二大爷刘海中更是背著手,抬头看天,仿佛那天上有花儿似的,就是不跟厨师对视。
开玩笑,许大茂醉死了,这钱谁给?谁掏谁是冤大头!这年头二十块钱那是小两个月的工资啊!
陈宇坐在主桌上,手里把玩著那个精致的银色打火机,“啪嗒”一声打开,“啪嗒”一声合上。他看著这尷尬且充满了算计的场面,心里嘆了口气。
这四合院里的人啊,吃肉的时候比谁都快,掏钱的时候比谁都慢。
虽然他不想当冤大头,但为了这个院子能儘快消停下来,也为了在许大茂醒来后让他欠个大人情,这钱,他得掏。
这叫“人情债”,最难还。而且,这也是他在新邻居和厨师面前立威、立德的好机会。
“师傅,辛苦了。”
陈宇慢悠悠地站起身,那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在一群衣衫襤褸的邻居中显得格外扎眼,那种鹤立鸡群的气质瞬间镇住了场子。
他从兜里掏出两张崭新的大团结,那是二十块钱,在冬日的阳光下闪著诱人的光泽。
“主家喝多了,这钱我替他垫上。今儿个菜做得不错,大家都挺满意的,特別是那道红烧肉,地道。”
胖师傅一看钱,眼睛都直了,立马眉开眼笑,点头哈腰地接过来,还在手指头上沾了唾沫数了数:
“哎哟,谢谢您嘞!您是个讲究人!一看就是领导!那是,咱们可是丰泽园出来的徒弟!那我们就撤了,您忙著!”
送走了厨师,陈宇转过身,看著这一院子的残局,脸一板,拿出了后勤干事兼纠察组长的威严。
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正在剔牙的刘光天和还在跟盘子较劲的阎解成:
“都吃饱了吧?吃饱了別閒著!光天、光福,还有解成,你们几个年轻力壮的,別光顾著长肉不干活!”
“把桌椅板凳都归置了,把地扫了!各回各家!別给主家添乱!吃人家的嘴短,这点活都不干?还得我请你们?”
吃了人家的嘴软,再加上陈宇现在的威信,这帮小年轻哪敢不听?一个个赶紧扔了牙籤,灰溜溜地动手收拾,生怕被陈宇记在小本本上。
这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
冬天的白天本来就短,这一顿饭从中午吃到了半下午,天色已经擦黑了。寒风一吹,酒足饭饱的邻居们也都感觉到了冷意,一个个缩著脖子,带著满嘴的油光,心满意足地回屋歇著去了。
整个大院,重新归於平静,只剩下空气中还残留著那股子诱人的肉香和劣质白酒的酒气,证明著刚才的狂欢。
陈宇走到桌子底下,看著睡得跟死猪一样、哈喇子流了一地、还时不时抽搐两下的许大茂,无奈地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戏謔的笑。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四大喜啊,许大茂啊许大茂,你这也是个人才。”
“娶了资本家的大小姐,那是多少人求不来的福分,结果你把自个儿喝成这样。我看你今晚这洞房怎么入,这娄晓娥,怕是要守活寡嘍。”
他弯下腰,一把將许大茂那一百多斤的身子架了起来。
许大茂死沉死沉的,浑身软得像麵条,嘴里还喷著臭气,陈宇皱了皱眉,屏住呼吸。
“走吧,茂爷,送你回宫。”
陈宇架著许大茂,一步一步穿过垂花门,往后院走去。
此时的天,已经有些黑了,四合院里昏黄的路灯亮了起来,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在斑驳的墙壁上晃动。
后院静悄悄的,只有许大茂家的新房窗户上,贴著大红的喜字,在夜色中透著股子喜庆,也透著股子讽刺。
陈宇扶著许大茂来到门口,许大茂还在那儿说梦话,手在空中乱抓,含糊不清地喊著:
“喝……接著喝……傻柱你不行……我是组长……我有钱……”
“闭嘴吧你。”
陈宇没好气地低喝一声,腾出一只手,整理了一下因为用力而有些微乱的衣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敲了敲门。
“篤、篤、篤。”
敲门声在寂静的后院显得格外清晰。
屋里立刻传来一阵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听得出来,里面的人等得很焦急,甚至带著几分新娘子特有的慌乱和期待。
“吱呀——”
门轴转动,发出一声轻响,房门被缓缓拉开。
一股温暖的热气混合著淡淡的、高级的茉莉花香粉味儿,顺著门缝扑面而来,与外面的寒风撞了个满怀。
陈宇下意识地抬起头。
只见门口站著一个身穿红色呢子大衣的年轻女人。
那是娄晓娥。
她烫著时髦的捲髮,皮肤白皙细腻,如同上好的羊脂玉,跟这院里那些面黄肌瘦的大妈大婶截然不同。灯光打在她那张略施粉黛的脸上,红扑扑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原本盛满了新嫁娘的羞涩和对丈夫归来的期待。
然而,当她的目光落在陈宇那张英俊却陌生的脸上时,明显愣了一下。
这人是谁?怎么这么精神?
紧接著,她的视线不可避免地下移,看到了掛在陈宇身上、不省人事、满身酒气还流著哈喇子、像一头死猪一样的许大茂。
那双漂亮的眼睛瞬间瞪大,瞳孔微微收缩,脸上的期待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凝固成了错愕、震惊,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失望和嫌弃。
两人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陈宇看著这新媳妇,又看了看这醉鬼,心里也是一阵无语。
这鲜花,还真插在牛粪上了,而且是一坨醉醺醺的牛粪。
他深吸一口气,脸上掛起那副標准的、人畜无害的温和笑容。刚想开口解释,结果脑子里还在想著怎么调侃这倒霉催的洞房夜,嘴一禿嚕,竟然喊劈叉了:
“嫂子,我是哥……”
话刚出口,陈宇就意识到不对。
这特么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是哥?那许大茂成啥了?我是你哥?还是我是你……那啥?
他赶紧“呸”了一口,差点咬著舌头,那张平时冷静的脸上罕见地闪过一丝尷尬:
“呸!嫂子,我是说……我是那个……许大茂的邻居,也是同事,我叫陈宇。那个……我扶大茂哥回来了。”
娄晓娥被这一声“我是哥”弄得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年轻人是在口误,但这口误……也太让人难为情了。
但看著陈宇那英俊挺拔的身姿,还有那刚才略显笨拙的解释,她心里那点失望竟然稍微淡了一些,反而觉得这人挺有意思,比那个只会吹牛的许大茂强多了。
她赶紧侧身让开路,那股子大小姐的娇气也被这突发状况给衝散了,手忙脚乱地去扶许大茂的另一只胳膊:
“哎呀,这……这是咋喝成这样了啊?快进屋,快进屋!麻烦陈干事了!真是不好意思,大喜的日子给您添麻烦了!”
一股淡淡的幽香再次袭来,陈宇心里微微一动。
两人合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猪一样的许大茂扔到了那张铺著崭新红被面、绣著鸳鸯戏水的婚床上。
“呼……”
许大茂一沾枕头,呼嚕声打得更响了,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鞋都没脱,满身的酒气和油烟味瞬间瀰漫了整个新房,熏得娄晓娥直皱眉,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眼里的嫌弃更重了。
陈宇站在床边,看著这幅场景,再看看旁边一脸无措、甚至有些委屈,正拿著手绢扇风的新娘子,忍不住在心里给许大茂点了根蜡。
这大喜的日子,让新娘子守活寡,还要伺候醉鬼,许大茂这事儿办得,確实挺“绝”的。这第一印象分,算是扣没了。
“那个……嫂子,大茂哥今儿个高兴,多喝了两杯。邻居们也都太热情了,没拦住。”
陈宇解释了一句,虽然这解释苍白无力,但也算是给许大茂留了块遮羞布,毕竟这还是人家的新房。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打火机,习惯性地把玩了一下,然后看著娄晓娥,语气平淡却周到:
“厨师那边的钱我已经结了,一共二十块。等他醒了你跟他说一声就行,不急著还。还有,这热水壶里有水,您给他擦擦脸,翻个身,省得明天起来难受,也別吐床上。”
娄晓娥看著这个英俊挺拔、谈吐不凡,而且行事如此周到的年轻干事,又回头看了看床上那头只会打呼嚕的死猪,心里不禁有了几分巨大的落差。
这就是许大茂说的“院里都是一般人”?
这陈宇,看著可不像一般人啊。这气度,比她见过的那些厂领导还要强。
“谢谢陈干事,那个……钱等大茂醒了,我一定让他还您。”娄晓娥低著头,声音轻柔,带著一丝感激,“今天真是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邻里邻居的,应该的。”
陈宇摆摆手,没有多做停留,转身向门口走去。
“那个……”
娄晓娥突然叫住了他,从桌上的喜盘里抓起两个红艷艷的红喜蛋,有些不好意思地递过来:
“陈干事,这喜蛋给您,沾沾喜气。您还没吃饭吧?”
陈宇回头,看著那双如水的眸子,笑著接过喜蛋,手指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娄晓娥那微凉的指尖。
娄晓娥像是触电一样缩回了手,脸更红了。
“谢谢嫂子。祝你们……早生贵子。”
说到“早生贵子”四个字时,陈宇的眼神若有若无地扫了一眼床上的许大茂,眼底闪过一丝戏謔。
这许大茂是个绝户命,这“早生贵子”,怕是这辈子都难了。而且今晚这洞房……悬嘍。
第152章 洞房花烛成死猪,且看陈宇戏晓蛾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