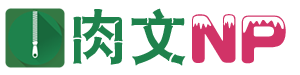黑色的panamera滑入夜色。
车厢里一片死寂,只有空调送风的轻响。
路明非像一滩烂泥,瘫在后排左座上,
苏晓檣坐在他身旁,也难得地没说话。
她抱著手臂,时不时眼神游移偷看一眼路明非。
车开得很稳。
楚子航握著方向盘,目不斜视,他就像一座不会疲倦的冰山。
“回去用热水泡脚,可以缓解肌肉酸痛。”
“明天早上起来可能会更疼,是正常现象。”
“听见没?”苏晓檣出声道,
“別明天瘸著腿去上学,丟人。”
她从自己的名牌包里翻了翻,扔过来一小瓶包装精致的红花油。
“喏,这个也给你。”
“別说本小姐不仗义。”
路明非勉强睁开眼,接住那冰凉的小瓶子。
“谢....”
“不许说谢。”
“那多谢了...小天女大人。”
“哼...”
“我还以为你要建议我再跑个五公里....以毒攻毒....”
“你就是个疯子。”
“彼此彼此,陪疯子练的,也不是什么正常人。”
“你说谁不正常!”
“谁应说谁。”
两人又开始了日常的拌嘴,但火力明显比平时弱了好几个档次。
主要是没力气。
车行驶在月色之下,
前面的面瘫师兄没有出声,眼神倒是时不时看后视镜。
而后方的少年少女各据一角,似乎各怀心思,
车窗开了一道缝,夜风钻进来,吹乱了苏晓檣额角的碎发。
她抬手,將那缕髮丝別到耳后,
侧头看向窗外飞逝的灯火,不知在想些什么。
城市的灯火在她清亮的眸子里拉出长长的光轨。
过了会儿,
视线又不自觉地飘了回来,
落在身旁少年的脸上。
他似乎真的累坏了,呼吸很轻,眉头却微微蹙著,
像是在梦里也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此时的他,没了平时说烂话的那股衰劲,也没了练剑时的那股疯劲。
安静下来,倒显出几分平日里看不见的乖巧和疲惫。
苏晓檣看著看著,眼神有些恍惚。
车身过弯,带起轻微的离心力。
原本就坐得不怎么稳当的路明非,身子隨著惯性晃了晃,顺势往旁边一倒。
不偏不倚。
意识朦朧间,
路明非只觉鼻尖嗅到了淡淡的清香,不是香水味,是洗髮水的清香,混著一点少女独有的、淡淡的甜味。
很舒服,很安心。
他靠著了什么,
像是小时候妈妈的枕头,
软软的,带著温暖的体温。
很舒服,像小时候晒得蓬鬆的枕头,又像是某种久违的怀抱。
“妈....”
苏晓檣身子猛地僵住。
她瞪大了眼睛,低头看著枕在自己肩膀上的那个脑袋。
路明非的脸压著她的颈窝,呼吸的热气喷洒在皮肤上,痒痒的。
本能地想抬手把他推开,再骂一句什么。
但在听到那声含混不清的“妈”时,
那只悬在半空的手,停住了。
她愣了一下,看著少年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还有眼底淡淡的青黑。
小天女咬了咬嘴唇,手慢慢落了下来。
没有推开,也没有掐他。
只是轻轻地,有些彆扭地,调整了一下坐姿,让他能靠得更稳当些。
“辛苦了....”
她小声嘟囔著,声音轻得连风都听不见。
前排。
楚子航收回视线,面无表情地把车內的空调温度调低了两度。
车子驶入隧道,光影斑驳地掠过三人的脸。
夜还很长。
....
不久后。
车子在路明非家小区门口停下。
苏晓檣家的车也跟在后面,司机早就在路边候著了。
路明非推开车门,感觉自己的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软得像麵条。
“餵。”
苏晓檣也下了车,视线却一直不敢看路明非,小脸还有些红,
她从包包里拎出电解质、风油精、绷带创可贴等乱七八糟的,一股脑胡乱塞进路明非怀里。
“喏,这个也给你,別明天猝死在教室了。”
她说完,不等路明非回话,就扭头走向自家的车,背影看著还有点同手同脚。
“路上小心。”
到达路明非家小区时,楚子航降下车窗,言简意賅地扔下几个字,
“明天,打算追加射击馆。”
然后发动了车子,黑色的panamera无声地滑入夜色。
“....”
不愧是楚子航。
....
路明非拖著两条灌了铅的腿往里挪。
回到家时,婶婶正敷著面膜在客厅看八点档的狗血剧。
看到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嫌弃地撇了撇嘴。
“又去哪儿鬼混了?看著跟被人打了一顿似的。”
“一身餿味,赶紧去洗了,別熏著屋里。”
路明非完全没搭理。
他现在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在那张硬板床上挺尸。
遂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
这种无视的態度瞬间点炸了婶婶。
她想起这几天这小子对家里人爱答不理的死样,心中火起。
以往那个唯唯诺诺、让他往东不敢往西的路明非哪去了?
“路明非!我跟你说话呢!”
婶婶猛地坐直身子,瓜子皮撒了一地,
“翅膀硬了是吧?叫你不应?去,把阳台衣服收了,再把地拖一遍!”
路明非脚步一顿。
他是真的烦了。
身体的极度疲惫加上脑子里还残留著那一千次挥剑的狠厉。
他猛地回头。
眼神没有任何遮掩,直直地扫了过去。
没有表情,没有言语。
只有那双因为极度专注而还未散去的、如刀锋般锐利的瞳孔。
那一瞬间,
婶婶仿佛看到的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穷侄子。
而是一头刚刚捕猎归来、满身血气的野兽。
或者是某种高高在上、俯视螻蚁的怪物。
“你....”
婶婶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
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脚底板直衝天灵盖,让她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她僵在沙发上,张著嘴,面膜都裂开了一道口子。
那个眼神太可怕了。
像是下一秒就要扑上来把她撕碎。
路明非並没有察觉到自己无意间泄露出的“龙威”。
他只是看了婶婶一眼,见她不说话了,便收回视线。
转身,推门,进屋。
“咔噠。”
房门反锁。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好半天,电视里的女主角发出了一声尖叫,才把婶婶惊醒。
她打了个哆嗦,这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是冷汗。
“神经病....”
她小声骂了一句,声音却虚得厉害,再也没敢去敲那个门。
....
屋內。
路明非整个人砸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脑海里,光幕准时亮起。
【一日修行结束。】
【现进行综合评估。】
【知识汲取:效率低下,存在分心现象。】
【体能锻炼:超负荷。】
【战斗技艺:突飞猛进。】
【君王仪態:尚可。】
【综合评价:c+。】
路明非眼皮跳了跳。
c+?
这还是他第一次拿到c以上的评价。
而且评语里居然有夸奖的词?
不爭这是吃错药了?
还没等他高兴。
【评语:一心多用,乃帝王之才。虽贪多嚼不烂,可意志可嘉。贪婪是君王的原罪,亦是前进的动力。请陛下保持。】
“保持你个头....”
路明非在心里骂了一句,意识便坠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
这一觉,他睡得死沉,连梦都没有。
——
夜色渐深。
楚子航坐在书桌前,檯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手边是管家刚送来的牛皮纸袋,里面装著路明非的资料。
很薄,几页纸就概括了一个衰仔的几年。
楚子航翻看著,面无表情,但捏著纸张的手指微微用力。
虽然早有耳闻,但白纸黑字写出来,还是让人觉得荒谬。
父母都是精英考古学家,常年在国外,寄回来的抚养费每个月都是一笔巨款。
但这笔钱,路明非一分都没见到。
全进了婶婶的口袋。
买了路鸣泽脚上的限量款球鞋,买了婶婶手腕上的金鐲子,买了叔叔那辆总是修不好的破车。
路鸣泽在学校成了泽太子,
而路明非呢?
楚子航合上资料,闭了闭眼。
难怪那天在小吃街,路明非说“不觉得不幸”。
因为已经习惯了。
他想帮路明非。
这对他来说很简单。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钱。
隨便找个名目,设个奖学金,或者以“有些旧装备没地方放”为由送他一堆东西。
甚至可以直接用家里的关係网施压,或者用法律手段就可以让婶婶一家把吞进去的钱吐出来。
但楚子航沉默了许久,还是没有选择现在出手,
不行。
以前或许可以。
但现在的路明非,不一样了。
他必须遵从他的想法,
少年意气,
他咬牙挥剑时的那种眼神,是有脊梁骨的人才有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直接贸然的施捨,哪怕是善意的,也可能会折断那根刚刚挺起来的脊樑,把他重新推回那个自卑的壳子里去,
等彻底熟识之后再施以援手是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让他自己来?
“路明非...”
楚子航看著窗外的月亮,低声自语。
既然你想靠自己站起来。
那我就只给你递刀,不给你递拐杖。
这才是对同类最大的尊重。
....
另一边。
苏家的大別墅里,中央空调吹著恆温的暖风。
苏晓檣把自己裹成个春卷,在两米宽的定製大床上滚来滚去。
睡不著。
根本睡不著。
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路明非。
是他挥剑时的汗水,是他背公式时的碎碎念,还有车上那个靠在她肩膀上、软绵绵喊“妈”的蠢样。
“啊啊啊!烦死了!”
小天女一脚踢开蚕丝被,抱著抱枕坐了起来,头髮乱糟糟的像个鸡窝。
“我怎么老想他....”
“苏晓檣,你清醒一点!那是路明非!是那个公公!是你以前觉得最可恶的傢伙!”
她拍了拍自己发烫的脸,试图把那些画面赶出去。
但没用。
怎么都挥之不去。
“不过....”
她抱著膝盖,下巴搁在抱枕上,眼神有些发直。
以前是死对头,所以她比谁都清楚路明非的底细。
全校都知道他寄宿在婶婶家,那个婶婶是个著名的泼妇,在超市抢打折鸡蛋能跟人打起来那种。
路明非在那过的是什么日子,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今天在道馆,她看见了。
路明非换下来的校服领口都磨破了,那双运动鞋的底都快平了,也不知道穿了几年。
练了那么久,连瓶像样的运动饮料都捨不得买,只喝免费的凉白开。
“笨蛋。”
苏晓檣嘟囔了一句,心里却酸溜溜的,有点不是滋味。
这么高强度的训练,营养跟不上怎么行?
回头没练成绝世高手,先把自己练废了。
“得帮帮他。”
这是小天女的第一反应。
她家是开矿的,最不缺的就是钱。
平时她买个包都要几万块,养个路明非还不是绰绰有余?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
现在的路明非,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且这傢伙脾气现在一看就倔的很,
要是直接拿钱帮他,说不定会被他当场扔回来,还得附赠几句阴阳怪气的烂话,
“伤自尊心这种事,本小姐才不干。”
苏晓檣咬著指甲,眨了眨大眼睛,
得想个法子。
....
第28章 我怎么老想他....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