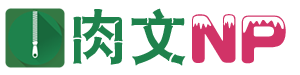夜色如墨,浓稠得化不开,將整个红星四合院浸泡在一片深不见底的死寂之中。
晚风停了,树叶不再沙沙作响,连平日里最爱聒噪的夏虫也在此刻噤声。空气仿佛凝固成一块沉重的铅,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院里大多数人家早已熄灯安睡,只有几扇零星的窗户里,还透出些许昏黄黯淡的灯光。那光晕在漆黑的背景下,並不显得温暖,反而像是蛰伏在暗处的野兽,正悄无声息地睁著眼睛,窥伺著猎物,为这本就压抑的氛围,平添了数不尽的诡异与森然。
傻柱,或者说,何雨柱,此刻就感觉自己是那只被窥伺的猎物。
他像一个找不到归途的孤魂,在四合院的阴影里游荡。他不敢走在月光下,只敢贴著冰冷的墙根,一步一步地挪动,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的心臟在胸腔里早已不是跳动,而是在疯狂地擂鼓,那“咚咚咚”的巨响是如此清晰,仿佛要震裂他的耳膜,下一秒就要从嗓子眼里生生蹦出来。
他怀里揣著的东西,比刚刚出炉的烙铁还要烫人,灼烧著他的皮肉,更灼烧著他的灵魂。
那是一沓厚厚的稿纸,纸张的边缘因他的紧张和汗水而变得有些柔软捲曲。
还有那张……那张足以要了何援朝老命的、决定一切的、致命的照片!
他做到了!
回想起半小时前的那一幕,傻柱的身体又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他这个在所有人眼里,尤其是在秦淮茹眼里,只会抡马勺的粗人、傻子,竟然真的办成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潜入了何援朝那个家,那个在他看来戒备森严,如同龙潭虎穴一般的地方。他像个最专业的小偷,撬开了阳台的插销,屏住呼吸,在那个属於何援朝的书房里,偷出了这些足以將那个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彻底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铁证!
在拿到东西的那一刻,一股巨大的、几乎要將他吞噬的恐惧,和一种病態的、即將大仇得报的狂喜,像两股截然相反的强劲电流,在他四肢百骸中疯狂地交织、乱窜。这两种极端的情绪撕扯著他的神经,让他浑身都在不受控制地发抖,牙关都在咯咯作响。
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巨大的成功感让他想要放声大笑,可深入骨髓的恐惧又让他想要跪地求饶。
他不敢回家,那个小小的、曾经带给他一丝温暖的家,此刻在他眼中却如同审判台。他甚至不敢在自家院里多停留一秒,总觉得每一扇黑暗的窗户后面,都有一双眼睛在盯著他,尤其是秦淮茹那双复杂的眼睛。
一想到秦淮茹,傻柱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尖锐地疼。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就是因为她吗?因为她对何援朝那毫不掩饰的亲近,因为何援朝轻而易举就夺走了他坚守了半辈子的阵地!他要证明,他何雨柱不是一个任人拿捏的傻子!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也能把那个不可一世的何援朝,狠狠地踩在脚下!
这个念头,如同地狱里伸出的手,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他不再犹豫,像一只被猎犬追赶到穷途末路的受惊老鼠,將身体压得更低,贴著墙根,借著夜色最浓重的掩护,猛地发力,一口气跑出了四合院的大门。
他没有回头,径直衝向了不远处的另一个院落,许大茂的家。
……
“咚!咚咚!”
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在万籟俱寂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如同催命的钟摆,一下下敲击在人的心上。
屋內,灯光“豁”地一下亮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许大茂极不耐烦,又带著浓浓警惕的声音。
“谁啊?大半夜的,敲丧呢?”
许大茂的声音压得很低,显然,他也知道这个时辰,这样的敲门声意味著什么。要么是天大的好事,要么,就是天大的祸事。
“是我!开门!”
傻柱用尽全力压低了声音,可喉咙早已因为极度的紧张和乾渴而嘶哑,发出的声音如同两片破锣在摩擦,难听至极。
屋里沉默了几秒钟。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狭窄的缝。
许大茂那张瘦削而阴鷙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昏黄的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让他看起来像个夜梟。
当他看清门外站著的,是脸色惨白、大汗淋漓的傻柱时,他先是猛地一愣,眼神里充满了惊愕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
可隨即,他的目光就捕捉到了傻柱那副失魂落魄,却又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极度兴奋的诡异表情。
许大茂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亮得嚇人!
那是一种饿狼闻到血腥味时才会有的光芒!
“进……快进来!”
他不再废话,一把抓住傻柱的胳膊,几乎是粗暴地將他拽进了屋里,隨即反手“哐当”一声,不仅关上了门,还死死地插上了门栓。
屋里陈设简单,空气中瀰漫著一股廉价菸草和煤油混合的呛人味道。
桌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安静地跳动著,火苗忽明忽暗,將两人的影子在粗糙的墙壁上拉扯、扭曲,变形,如同两只正在密谋的鬼魅。
“怎么样?得手了?”
许大茂的声音克制不住地微微发颤,他甚至没给傻柱喘息的机会,一双贼眼如同探照灯一般,死死地锁定在傻柱胸前那鼓囊囊的衣怀里。
傻柱没有立刻说话,他背靠著冰冷的门板,胸口剧烈地起伏著,像是刚跑完一场马拉松,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气,试图將那颗快要爆炸的心臟给压回去。
过了许久,他才缓缓直起身,走到桌边,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了那沓厚厚的、被他手心的汗水浸得有些潮湿发皱的稿纸,和那张被他捏出摺痕的照片。
他將两样东西“啪”的一声,一把拍在了桌子上!
“你……你自己看!”
许大茂的呼吸,在这一瞬间,彻底急促了!
他像一头被饿了三天三夜的野狼,猛地扑到桌前,眼中迸发出贪婪的光芒。
他没有先去看那张薄薄的照片,而是迫不及待地,先拿起了那沓沉甸甸的稿纸。在他看来,能被何援朝锁在书桌里的文字,必然是什么见不得光的日记,或者与海外的通信。
他飞快地翻阅起来。
稿纸上,是何援朝那笔走龙蛇、气势磅礴的字跡,每一个字都透著一股强大的自信和力道。
但稿纸上的內容,却让许大茂的脸色一点点地沉了下去,兴奋的潮水迅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失望和愤怒。
什么“关於提高轧钢效率的几点技术构想”……
“论齿轮传动中的动载荷係数与材料疲劳极限的关係”……
“车间自动化流水线流程初探与设想”……
满篇,全都是他一个字也看不懂的、鬼画符一样的技术名词、复杂的公式推演,以及精密到让他头晕眼花的机械图纸!
“妈的!这孙子,装什么大尾巴狼!在家里都不干点別的,就他妈琢磨这些没用的破玩意儿?”
许大茂失望透顶,像丟垃圾一样,將那沓在他眼中一文不值的稿纸狠狠地摔在桌上,咒骂声从牙缝里挤了出来。他感觉自己被耍了,被傻柱这个蠢货给耍了!
他的目光,隨即无可奈何地,落在了那张被遗忘在一旁的、薄薄的、看似毫不起眼的照片上。
他抱著最后一丝希望,或者说,是为了证明傻柱到底有多蠢,才將这张照片拿了起来,凑到摇曳的煤油灯下。
灯光昏黄,照片是黑白的。
然而,当照片上那清晰的、足以让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魂飞魄散的画面,一寸一寸地映入他眼帘的瞬间——
许大茂的瞳孔,猛地收缩成了最细、最危险的针尖状!
他脸上的表情,经歷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剧变。从最初的失望与不屑,瞬间凝固,然后龟裂,最后,被一种极致的、几乎不敢置信的狂喜所彻底取代!
照片上,背景似乎是在一间办公室里。
年轻的何援朝穿著一身普通的工装,脸上带著无比灿烂、甚至有些刺眼的笑容。
而他的那只手,竟然无比亲密地,搭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
那个男人,穿著一身笔挺的、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军官制服,领章上,那“青天白日”的徽章在照片里依旧清晰可辨!
那赫然是一名国民党军官!
如果说这还能用“被胁迫”来解释,那么两人身后,墙壁上悬掛著的那面巨大的、无比刺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彻底封死了所有的退路!
旗帜,清晰可见!笑容,清晰可见!亲密的动作,清晰可见!
“我……我操……”
许大茂只觉得一股冰冷的电流,从他的尾椎骨“轰”的一声直衝天灵盖!他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仿佛都凝固了,紧接著又疯狂地沸腾起来!每一根汗毛,都因为这极致的刺激而根根倒竖!
他拿著照片的那只手,抖得像是深秋寒风中最后一片枯黄的落叶,几乎要拿捏不住。
这……这是什么?!
这他妈的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黑料”了!
这是通敌!是私通反动派!是与人民为敌!
这是铁证如山的……反革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许大茂先是愣了足足有半分钟,整个人如同被定住了一般。隨即,他的胸腔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不住的、如同夜梟般尖利而疯狂的大笑!
那笑声在狭小的房间里迴荡,充满了得意、怨毒和一种大仇得报的畅快淋漓。
他笑了!
他终於可以放肆地笑了!
这段时间以来,被何援朝压製得抬不起头的憋屈,在厂里被人指指点点的耻辱,在这一刻,尽数烟消云散!
他知道,自己贏了!
彻彻底底地贏了!
有了这张照片,別说何援朝只是一个区区的工程师,他就是轧钢厂的厂长,是主管工业的市领导,也只有死路一条!
他甚至能清晰地预见到何援朝的下场:被立刻打倒!掛上牌子,戴上高帽,进行全厂批斗!在所有同事、邻居鄙夷和愤怒的目光中,被拉去游街!然后,所有的功勋、荣誉、地位、財富被一扫而空,像一条死狗一样,被送去遥远的青海劳改农场,在那片不毛之地上,挖一辈子的土豆!永世不得翻身!
“傻柱!傻柱!你他妈的真是我的福星啊!”
许大茂激动得语无伦次,一把抱住还没从惊魂和疲惫中完全回过神来的傻柱,用尽力气在他宽厚的后背上狠狠地拍著,发出“砰砰”的闷响。
“有了这个!何援朝死定了!耶穌来了都留不住他!我说的!”
傻柱被他拍得生疼,齜牙咧嘴,但心里,同样也涌起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復仇的快感。何援朝倒了,秦淮茹就没有念想了,是不是……就会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这个念头让他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看著许大茂那张因狂喜而彻底扭曲变形的脸,沙哑著嗓子问道:“那……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天一亮,直接把这照片交到厂保卫科去?”
“不!不能这么简单!”
许大茂鬆开傻柱,他的眼睛里,闪烁著毒蛇般阴冷而恶毒的光芒,那光芒比桌上的煤油灯还要亮。
“直接交上去,太便宜他了!那只是让他死,不够!我要让他,在死之前,身败名裂!”
他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乾裂的嘴唇,脸上浮现出一种病態的、无比亢奋的潮红。
“你忘了?明天!就是明天!厂里就要在宣传栏上,公示新一届『先进生產者』的名单了!以何援朝最近的风头,他的名字,肯定在第一个!最醒目的位置!”
“我们,就在明天早上,所有人上班的时候,在全厂最大的那个宣传栏上,给他贴一张最大的、最醒目的大字报!”
许大茂的声音变得尖锐而兴奋,他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即將到来的胜利。
“我要去放映科,把这张照片,放大!放大到最大!清清楚楚地贴在大字报的最中央!我要让全厂几千號人,都停下来,都来好好看看!看看他们眼里那个高不可攀的『技术大神』,那个所有人都敬佩的『先进標兵』,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然后,我们再准备另一份材料,把这些『废纸』也附上,证明他心怀不轨,图谋不轨!直接越过厂里,送到市革委会去!我他妈就不信,这天罗地网,他何援朝长了翅膀还能飞了不成?!”
许大茂的计划,恶毒到了极点!
他不仅要彻底毁了何援朝的政治生命和未来,他还要在他声望达到顶峰的那一刻,用最公开、最羞辱、最惨烈的方式,將他从云端狠狠地拽下来,再一脚踩进最骯脏的泥里,让他受尽所有人的唾骂和鄙夷,让他一辈子都活在耻辱的烙印里!
这,才是他许大茂想要的復仇!
“好!就这么办!”
傻柱也被许大茂描绘的这幅场景所感染,他紧握的拳头狠狠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煤油灯都跳了一下。他的眼神里,是破釜沉舟的狠厉!
两个被嫉妒和仇恨彻底冲昏了头脑的男人,就在这间昏暗油腻的屋子里,就著那沓被他们当成“废纸”,实际上却对国家工业发展价值连城的技术手稿,开始连夜炮製那封足以在红星轧钢厂掀起滔天巨浪的……死亡判决书。
他们沉浸在即將到来的胜利狂欢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
在他们头顶的、那无尽的、仿佛能吞噬一切的黑暗之中,正有一双冰冷的、洞悉一切的、如同神明般的眼睛,在静静地注视著这一切。
……
与此同时,干部楼,何援朝的家中。
与许大茂那里的阴暗、齷齪截然不同,这里灯光明亮,窗明几净。
何援朝、娄晓娥、何雨水三人,已经从电影院看完成功的夜场电影,回到了家。
屋里的气氛一片温馨和谐。
娄晓娥正在厨房里给何雨水削苹果,果皮在她的巧手下连成一条长长的线,姐妹俩一边聊著电影里的精彩情节,一边不时地发出一阵阵清脆悦耳的笑声。
客厅里,何援朝脱下外套,掛在衣架上,然后不紧不慢地,走进了书房。
“咦?”
娄晓娥听到书房的门响,有些奇怪地探出头问道:“援朝,你书房的门怎么是开著的?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你特意锁好了呀?”
“是吗?可能是我记错了。”
何援朝的语气平静如水,听不出丝毫的波澜。
他走进书房,目光如同平静的湖面,在空空如也的书桌上轻轻扫过,然后,又落在了阳台那扇玻璃门上,那被人从里面拨开的插销锁,在灯光下反射著冰冷的光。
一切,尽在掌握。
他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意味不明的弧度。
鱼儿,终於还是咬鉤了。
“援朝,怎么了?是不是……是不是丟东西了?”
娄晓娥也走了过来,当她看到那张空荡荡的书桌时,脸色瞬间就变了,声音里充满了紧张。
那些稿纸,可都是何援朝熬了无数个夜晚,耗费了无数心血才写出来的啊!
“没丟。”
何援朝转过身,面对满脸担忧的妻子,脸上露出一个足以安抚人心的笑容。他的声音里,是强大的、足以抚平一切不安的自信。
“它们没有丟。”
“它们只是……去了一个它们应该去的地方。”
他顿了顿,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望向了许大茂家的方向,声音轻得如同耳语。
“去履行,它们最后的使命了。”
说著,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那个抽屉,从抽屉的最深处,拿出了另一沓一模一样的、字跡分毫不差的稿纸,和另外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
然后,他將它们,整齐地、一丝不苟地,重新摆放在了书桌的正中央。
仿佛,这里的一切,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娄晓娥,却从自己丈夫那双深邃平静、宛如古井的眼眸深处,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一闪而过的、凛冽的、即將出鞘的……杀意!
第107章:娄晓娥的恐惧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