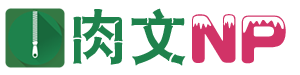李天佑和其他司机被带到了仓库旁边的一间空房里,逐个被单独盘问。“昨晚你几点睡的?”“有没有离开过招待所?”“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和仓库的人有没有过接触?”
同样的问题,李天佑被问了三次。每次他都平静地回答:“昨晚八点多就睡了,和小陈住一个房间,他可以作证。中途没离开过招待所,也没听到什么异常动静。”
和他一起的司机们也都口径一致。昨晚车队抵达后,大家累了一天,吃过饭就回招待所休息了,互相之间都能作证,確实没人离开过。
公安人员反覆核实,调取了招待所的登记记录,又询问了招待所的服务员,確认司机们所言非虚。
仓库的看守和工作人员也被轮番盘问。他们一口咬定,昨晚锁好了仓库大门,巡逻时也没发现异常,库房的门窗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破门而入的痕跡。
院子里的车辙印只有车队和之前那五辆卡车的,没有其他运输工具进出的跡象。
三百吨粮食,不是小数目,就算用十辆卡车,也得装好几趟才能运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公安人员在仓库里仔细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却始终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库房的墙壁没有破损,地面没有新的车辙,通风窗的铁丝网虽然有被撬动的痕跡,但上面的灰尘太厚,看不出新鲜的指纹。
调查持续了一整天,太阳从东边升到西边,又渐渐落下,仓库里依旧一片混乱。公安人员、公社干部、仓库人员和车队的人都疲惫不堪,却毫无头绪。
最后,实在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只能將案件定性为 “內部监守自盗,里应外合”。毕竟,能用这种悄无声息的方式一夜搬空仓库的,只有熟悉仓库布局、掌握钥匙、知道粮食存放位置的內部人员。
“肯定是你们仓库內部有人勾结外人,把粮食运走了!” 公安人员拍著桌子,对仓库的负责人说,“我们会继续调查,但你们也得配合,把所有工作人员的社会关係都梳理一遍,尤其是昨晚值班的人!”
仓库负责人脸色煞白,连连点头,心里却叫苦不迭,他知道,这事儿大概率是说不清了,能不能找到粮食还是未知数,他这个负责人的乌纱帽,恐怕是保不住了。
傍晚时分,车队终於被允许离开。车子驶出仓库大院时,李天佑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仓库门口依旧围著不少人,警戒线还没撤,气氛依旧凝重。
回北京的路上,车队里的气氛压抑得可怕。没有一个人说话,驾驶室里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车轮碾过路面的声响。
每个司机都心事重重,脸上带著劫后余生的庆幸,又夹杂著对那批失踪粮食的疑惑。好好的一批粮食,怎么就凭空消失了?这事儿太过诡异,让人心里发毛。
李天佑坐在副驾驶座上,目光平静地看著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冬日的华北平原一片萧瑟,枯黄的野草被寒风颳得瑟瑟发抖,光禿禿的树木孤零零地立在田野里,透著一股绝望的气息。
偶尔能看到几个村民,佝僂著身子,在已经收割过的地里仔细翻找著,像是在寻找遗漏的红薯根、玉米芯,哪怕是一点点能果腹的东西。他们弯腰的姿势,充满了对食物的渴望,也充满了生活的绝望。
他的手悄悄揣在口袋里,握著一把从空间里取出来的大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带著淡淡的米香,是真正的上等粮。这把米,是那些特供干部们不屑一顾的日常,却是无数百姓梦寐以求的救命粮。
“李队。” 年轻司机小陈忽然开口,声音乾涩沙哑,打破了车厢里的沉默。他握著方向盘的手紧了紧,眼神里满是困惑,“您说......那批粮,会到哪儿去呢?三百吨啊,怎么就能说没就没了?”
李天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似乎更冷了,吹得车窗微微作响。他看著那些在地里翻找的村民,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 他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但我知道,拿这种救命粮食发財的人,迟早会遭报应的。”
小陈点点头,不再说话。他也想到了家里的情况,粮食越来越紧张,父母已经开始挖野菜充飢了。那批失踪的细粮,要是能分到普通百姓手里,该能救多少人啊。
卡车继续行驶在通往北京的公路上,夜色渐渐降临,远处的灯光星星点点。李天佑闭上眼睛,意识沉入空间。
那座新出现的粮山静静佇立在虚空里,雪白的大米、金黄的麵粉、沉甸甸的油桶,堆得像一座小山,旁边是他这两年攒下的各种物资 —— 布匹、药品、农具,还有之前接济百姓剩下的粮食。
整整三百吨。他在心里算了一笔帐:按每人每月十五斤口粮算,这些粮食够四千人吃一个月;要是省著点吃,够四百人吃十个月。这可不是小数目,能让很多人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他想到了 95 號院,想到了整条南锣鼓巷,想到了孙石头,—— 孙石头伤了手,家里五个孩子,全靠孙妻打零工勉强
餬口;想到了李算盘,那个在垃圾堆里捡白菜帮子的老人,手里还攥著一本写满菜谱的笔
记本;想到了赵老倔,那个耿直的老兵,在仓库里看夜,每月的粮票勉强够自
己吃;还想到了那些面黄肌瘦的邻居孩子,想到了纺织厂门口那些找工作的失业者,想到了河北乡下那些在地里翻找食物的村民。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救一个是一个。能多救一个人,这险就没白冒,这事儿就没做错。”
远处的北京城轮廓渐渐清晰,巍峨的城楼在夜色中隱约可见,城楼上的红旗在寒风中
飘扬。1959 年的冬天才刚刚开始,寒冷和飢饿还会持续很久,还会有很多人在生死边缘挣扎。但李天佑知道,那些被他 “带走” 的粮食,將会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让有些人能够稍微暖和一点、稍微不那么飢饿地活下去。
卡车驶过永定门,李天佑最后看了一眼后视镜。镜子里,大兴县的方向早已消失在漫天尘埃中,就像那个红星仓库里,从未存在过三百吨粮食一样。
没有人知道那些粮食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他昨晚做了什么。这个秘密,將会永远埋藏在他心底。
只有他知道,那些粮食现在在哪里。
以及,它们將要去, 去向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去向那些在寒冬里苦苦挣扎的百姓心里。
数九寒天的腊月很快到来,北风卷著碎雪沫子刮过南城天桥一带的老街道,墙根的残雪结著冰碴,光禿禿的槐树枝椏在风里晃悠,把天晃得更显阴沉。
街边的悦来茶馆,是打前清就立著的老铺子,朱红门脸早褪成了暗褐,边角翘著皮,两扇木门推起来吱呀作响,脚下的青石板门槛被几十年的鞋底磨得溜光水滑,嵌著几道深浅不一的纹路,藏著满街的烟火与故事。
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日头斜斜地掛在西边,没半点暖意,茶馆里却透著股闷出来的热气。挑高的屋樑下悬著盏昏黄的煤油灯,灯芯烧得滋滋响,映著墙上斑驳的旧年画,边角卷著边,看不清眉眼。
里头的茶客清一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裹著浆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有的扣著盘扣,有的扎著粗布腰带,袖口磨出了毛边,一人占著一张粗木方桌,面前摆著豁了口的粗瓷茶碗,壶里泡的都是最实惠的高末,茶叶沫子沉在碗底,抿一口暖身,就能喝上半晌。
老茶客们的话头从没断过,声音都压得低低的,怕惊了这茶馆里的静,也怕外头的风听了去。从康熙爷微服私访的掌故,扯到民国时天桥的杂耍班子,再绕到如今手里攥著的粮票布票,说者嘆著气,听者皱著眉,偶尔有人接一句“这年月,啥都紧俏”,便引来一片低低的附和,茶碗碰著桌沿,发出轻悄悄的响,混著茶烟,在屋里绕来绕去。
忽然,茶馆的厚重棉门帘被人从外头掀开,一股刺骨的寒风裹著雪沫子钻进来,惹得靠近门口的老茶客缩了缩脖子,抬眼瞥了一下。
掀帘子正是李天佑,他抬手拢了拢头上的黑棉帽,把帽檐压得稍低,挡了挡眉眼,进门后反手把棉门帘拽严实,门帘上的棉絮蹭了蹭他的肩头。
一股混杂著陈年茶垢的涩味、灶膛里的煤烟味、老木头桌凳的霉干味,还有点茶客身上的皂角味,一股脑扑面而来,裹著茶馆里的热气,扑在他冻得发红的脸上。
他穿一身运输队的藏青蓝布工装,褂子上沾著点淡淡的煤渣,袖口挽著,露出腕上一道浅浅的疤痕,裤脚塞在棉鞋里,鞋帮上沾著泥点,看著就是个整日在外跑活的普通工人,混在天桥的人堆里,半点不扎眼。
柜檯在茶馆进门的左侧,黑檀木的柜檯磨得发亮,掌柜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脸上刻著沟壑似的皱纹,下巴上留著一撮山羊鬍,正低著头拨拉著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响,在低低的说话声里,倒成了茶馆里的调子。
他听见动静,抬眼掀了掀眼皮,扫了李天佑一眼,没说话,手指依旧在算盘上起落,算珠碰撞的脆响,一下下敲在静气里。
李天佑没往茶客堆里去,径直走到柜檯前,脚步放得轻,声音也不大,压著嗓子喊了声:“掌柜的。” 掌柜的算盘珠子顿了一下,眼皮又抬起来,目光落在他脸上,还是没吭声。
“买二两大前门。”李天佑又说,语气平淡,听不出半点异样,就像寻常买烟的主顾。 这话一出,掌柜的拨算盘的手彻底停了,手指搭在最末的一颗算珠上,抬眼看向他,眉头微蹙,慢悠悠问:“什么年月產的?”
茶馆里的说话声似乎又低了几分,有老茶客端著茶碗,余光悄悄瞟过来,又飞快地转了回去,假装继续听旁人扯閒话。
李天佑的目光落在柜檯后的茶罐上,罐子上的青花早褪了色,嘴里依旧是那一句,字字清晰:“要去年腊月的。”
掌柜的这才直起身子,身子往柜檯前凑了凑,浑浊的眼睛仔仔细细打量了他一番,从压著的棉帽檐,到沾著煤渣的工装,再到他冻得发紫的手指,看了足有两三秒,才缓缓移开目光。
手慢慢伸到柜檯底下,在一堆纸包、烟盒里翻了翻,摸出半包皱巴巴的大前门,烟盒纸有些发软,他用手指推到李天佑面前,声音压得极低,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腊月的就剩这些了,搁久了受潮,菸丝发绵,不好抽。”
李天佑伸手接过烟,指尖触到微凉的烟盒,他的手指在烟盒底部轻轻摩挲了一下,触到一道浅浅的刻痕,三横一竖,像个简易的“王”字,刻得浅,不仔细摸根本察觉不到。
他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快得像风拂过水麵,隨即点点头,没说话,从工装內兜掏出几张毛票,放在柜檯上,票子被手心的热气焐得发软。
掌柜的瞥了眼钱,依旧没吭声,低头继续拨拉算盘,噼里啪啦的声响,又响了起来。李天佑捏著烟,转身就走,再掀棉门帘时,比进来时更急了些,寒风裹著雪沫子再次灌进来,这次,没人再抬眼。
出了茶馆,北风正紧,颳得街边的电线桿呜呜作响,像有人在耳边低嚎,风卷著雪沫子打在脸上,生疼。街对面的供销合作社门口,排著老长的一队人,从门口一直绕到了巷口,都是附近的街坊,一个个裹著厚棉袄、扎著围巾,缩著脖子在风里等著,都是来买晚饭的配给菜的。
队尾的老太太,头髮花白,裹著条灰扑扑的围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怀里紧紧抱著个蓝布兜,兜口用麻绳扎著,露出半截蔫巴巴的白萝卜,萝卜皮皱著,带著点冻痕,是这年头难得的菜蔬。
第372章 联繫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