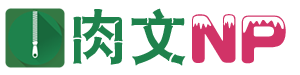旧帝国的幽灵在维也纳这座城市之中徘徊,未来的不確定性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
在这日益激化的政治对立中,越来越多的奥地利男男女女开始被捲入愈发膨胀的漩涡。
纺织女工玛利亚拖著疲惫不堪的身体,下班后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间由社会民主党开设的、位於工人区地下室里的夜校。
站在讲台上的一位年轻讲师,
“同志们,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在粉尘里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换来连一件像样大衣都买不起的工资?
为什么工厂主的孩子可以去滑雪,我们的孩子却要在冬天挨冻?这不是天经地义的!”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属於我们自己!这不是施捨,这是我们应得的权利!工厂的机器是我们开动的,財富是我们创造的,我们理应拿回属於我们的一部分!”
玛利亚看著周围那些和她一样面黄肌瘦的工友们思考著。
“他们说的有道理,”
玛利亚喃喃自语,
“我们为什么要像牲口一样被使唤,却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那一刻,对公平和尊严的本能渴望,压过了长久以来的麻木与顺从。她在心底,为那面红色的旗帜留下了一个位置。
与此同时,在那家被砸的纺织店里,店主弗兰茨·胡贝尔 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他正小心翼翼地用报纸糊住橱窗的裂缝。
弗兰茨·胡贝尔看著报纸上“家园卫队”与“共和保卫联盟”衝突的照片,以及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承诺“恢復法律与秩序”、“保护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演讲,內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全感。
“社会化?”
弗兰茨·胡贝尔对著空荡荡的店铺苦笑,
“说得真好听,不就是抢走我辛辛苦苦经营了二十年的小店吗?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是我起早贪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下来的!”
弗兰茨·胡贝尔想起那些穿著工装、喊著激进口號的年轻人从店门前经过时投来的目光,那目光让他感到自己的小店铺和微薄的积蓄仿佛成了某种原罪。
“秩序,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秩序。”
弗兰茨·胡贝尔对自己说,仿佛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儘管他对基督教社会党那些极端分子的一些排犹言论也有所保留,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寧愿选择一个承诺保护像他这样的小有產者的“秩序维护者”,而不是那些想要“砸烂一切”的“革命家”。
弗兰茨·胡贝尔將一张印有塞佩尔神父头像的传单,郑重地压在了柜檯玻璃板下。
而在维也纳一所文法中学的教师休息室里,年轻的埃里希·莫泽 则被另一种愿景所吸引。他教授歷史和文学,对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荣光与如今的衰败感触尤深。
他看著课堂上那些营养不良、眼神迷茫的学生,看著地图上那个被割裂、缩水得不成样子的奥地利,一种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和对强大归属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
大德意志人民党的宣传海报上,那雄鹰徽章和“一个民族,一个帝国!”的標语,深深地触动了他。
课间,他与一位和他一样年轻的同事靠在窗边,望著阴沉的天空,低声討论著:
“埃里希,你真的认为德奥合併是出路吗?”
埃里希·莫泽转过头,眼中闪烁著理想主义的光芒:
“为什么不行?看看我们!一个被阉割的国家,一个没有灵魂的共和国!我们和北边的德意志同胞,说著同样的语言,有著同样的文化血脉。为什么我们要被困在这阿尔卑斯山的角落里,独自承受这一切?
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红色的德意志,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回尊严和力量!
这不仅仅是政治,这是歷史的必然,是民族的宿命!”
在埃里希·莫泽的想像中,一个超越了旧帝国、由劳动人民组成的伟大德意志,能够洗刷战败的耻辱,能够带来真正的復兴。
他对那个模糊但宏大的“大德意志”梦想,心驰神往。
在这个经济彻底崩溃、政治严重分裂的国家里,无数迷茫的奥地利人正在绝望中摸索著自己和国家未来的出路。
没有人能看清前方的道路,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国家正在分裂,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强。
维也纳那些依旧飘著咖啡香气的咖啡馆里,穿著旧式燕尾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忧心忡忡地交换著眼神,低声谈论著一个越来越常被提及的词汇:
“burgerkrieg”——內战。
这个曾经只存在於书中的词语,如今正悄然逼近维也纳,逼近每一个奥地利人的生活。
巴黎,法国政府內部会议。
“先生们,维也纳的混乱,对我们而言不是麻烦,而是机遇。一个团结的、尤其是倾向柏林的奥地利,是法兰西枕边的噩梦。
但现在,奥地利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克列孟梭拿起一份关於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及其“家园卫队”的详细报告。
“这个塞佩尔神父,还有他手下那群喊著反犹口號、梦想恢復『秩序』的暴徒,是我们最好的工具。”
外交部长谨慎地接口:
“总理先生,直接介入风险很大。如果被曝光我们资助奥地利的右翼民兵……”
“那就不要被曝光!”
克列孟梭粗暴地打断了他,
“我们不是在指挥一支军队,我们是在『灌溉』一片充满潜力的土地。通过瑞士的银行,用那些无法追踪的帐户,把法郎像种子一样撒出去。
把我们库存的那些『多余』的武器,通过黑市渠道,『流失』到『家园卫队』手中。我们要让他们有力量去对抗,去製造更大的混乱。”
陆军部长接著说道:
“我们在维也纳的人报告,『家园卫队』缺乏训练和重型装备。我们可以安排一些『退役』的军官,以个人身份担任顾问,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街头格斗和小组战术。
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建立情报网络,精准打击社民党。”
情报负责人补充道:
“舆论上也需要引导。我们已经通过几家看似中立的瑞士和匈牙利报纸,开始將社民党和大德意志人民党描绘成『柏林代理人』,將他们的主张定义为『出卖奥地利主权』。
同时,隱晦地讚扬基督教社会党是『传统价值的捍卫者』。我们需要在奥地利人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让他们恐惧北边的德国。”
克列孟梭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的策略很清晰:资金、武器、顾问、舆论,四位一体。
我们要让基督教社会党这只拳头足够硬,硬到能把维也纳的街头变成战场,能把奥地利的议会变成废墟。
一个陷入內战、无暇他顾的奥地利,一个让柏林不得不分散精力去处理的『烂摊子』,才是一个符合法兰西利益的奥地利。”
维也纳,一家僻静的古董店后室。
法国特使 皮埃尔·瓦莱正悠閒地坐在一张路易十五风格的扶手椅上。
坐在他对面的,是 奥托·克劳斯,基督教社会党內的实权人物,伊格纳兹·塞佩尔神父最信任的左右手之一。
“克劳斯先生,”
瓦莱用流利的德语开口,
“希望您最近一切顺利。维也纳的春天,总是带著一种令人不安的躁动,不是吗?”
克劳斯微微前倾身体,
“瓦莱先生,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来討论天气了。
维也纳的躁动正在吞噬我们。社民党的红色民兵越来越猖獗,还有那些喊著要併入柏林的大德意志狂热分子……奥地利的秩序正在崩塌。”
瓦莱轻轻掸了掸雪茄灰,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秩序……是的,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法兰西深切理解並讚赏贵党为恢復秩序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始终认为,一个稳定、独立的奥地利,是维持中欧和平的基石。”
“讚赏需要体现在行动上,瓦莱先生。”
克劳斯直截了当,
“『家园卫队』的年轻人有满腔热血,但热血无法对抗子弹。我们需要武器,需要经费,需要让我们的声音能够压过街头的那些红色口號。”
“当然,”
瓦莱从容不迫地从內袋取出一个朴素的信封,推到书桌中央,
“一点小小的『印刷费』,用於支持贵党的……舆论宣传。来自一些同情奥地利事业的法国『友人』。”
克劳斯拿起信封,看也没看就塞进西装內袋,动作乾脆利落。
“舆论很重要,但手中的武器更重要。我们的人需要能在巷战中压制对方的装备。”
“关於这一点,”
瓦莱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一批『农业机械』的零部件,將会通过的里雅斯特的渠道,混杂在义大利的货物中运抵。
我相信,贵党的工程师们知道如何將这些……『零部件』,组装成有效的『除草工具』。”
克劳斯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我们有很多亟待『清理』的杂草。但是,光有工具还不够,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才能解决国內的棘手问题。”
瓦莱点点头,“我们有专业人士,可以『顾问』的身份,为贵党提供必要的培训和信息。”
“很好,”
克劳斯露出一丝狰狞的笑意,
“请转告巴黎的朋友们,奥地利不会忘记在困难时伸出援手的朋友。我们会让维也纳,让整个奥地利,恢復它应有的面貌和秩序。那些试图玷污它、分裂它的人,將会付出代价。”
瓦莱举起酒杯,里面晃动著琥珀色的白兰地:
“为了奥地利的未来,为了……秩序。愿我们的合作,能驱散这片土地上的阴霾。”
两只酒杯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一场將把奥地利进一步推向血与火的交易,在这间静謐的密室里达成了共识。
第163章 奥地利的战后情况2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