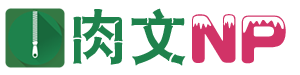在採访了乞丐之后,斯诺將目光投向了巴黎“赤区”的核心地带——第十八区蒙马特高地附近。
在一条被改名为公社战士街的巷口,他遇到了正在指挥工人纠察队(赤卫队)设置路障检查点的亨利。
亨利与杜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的身材矮壮敦实,右脸颊有一道明显的、发白的疤痕,从颧骨延伸到下巴,那是战爭留下的印记。
他穿著一身洗得发白但乾净整齐的蓝色工装,臂戴鲜红的“人民自卫委员会”袖標,腰间束著武装带,上面掛著一个旧水壶和一盏煤油风灯。
斯诺表明身份和来意后,亨利没有立刻答应,而是仔细检查了他的证件,又用盘问了斯诺几句,才点了点头,示意斯诺跟他走到路边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那里摆著两张从附近咖啡馆搬出来的旧椅子。
“美国人?来听故事?”
“也好。让外面的人知道知道,法兰西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对我们这些人干了什么。”
他掏出一个铁烟盒,自己卷了支烟,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繚绕中,他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时空,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泥泞战壕。
“故事?我的故事,开始於马恩河,”
“1914年,我二十岁,是个里昂的钳工。像所有傻小子一样,被保卫祖国、对抗德国佬的口號煽得热血沸腾。
我们唱著《马赛曲》上了火车,以为几个月后就能带著荣耀回家。”
他吐出一口烟,冷笑一声,
“荣耀?我们在凡尔登的泥浆和血肉里泡了两年。德国人的炮弹,我们长官的愚蠢命令,还有战壕里老鼠和坏疽,杀死了我连队四分之三的人。
我脸上的疤,就是拜一块该死的炮弹碎片所赐。
我在野战医院躺了三个月,醒来时,战爭结束了。”
“他们给我们发了点微薄的遣散费,一枚勋章,还有一堆空话:
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光荣的退伍军人。
然后呢?然后就把我们像破扫帚一样扔回了社会。
我回到里昂,原来的工厂位置没了,被更年轻的人顶了。
我找工作,僱主看看我的疤,听听我因为毒气有点喘的肺,就摇头。那点遣散费也很快花光了。”
毒气的语气平静得可怕,
“我的老婆在我在前线时,跟別的男人,跑了。
我不怪她,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来。但我只剩下自己了。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退伍兵,住在廉租房里,靠打零工和一点点可怜的伤残补助过活。
我们开始聚会,喝酒,骂娘。慢慢地,我们组织起来,要求政府兑现承诺:
像样的工作,体面的抚恤,医疗照顾。
我们以为,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它至少该给我们一条活路。”
说到这里,亨利的眼睛骤然缩紧,手中的烟被捏得微微变形。
“1921年春天,我们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请愿游行。
老兵,还有失业的工人,好几千人。我们很守秩序,举著標语,喊著麵包与工作、尊重牺牲者。
我们走到共和国广场附近……” 他停顿了很久,
“警察来了。
骑著马,拿著警棍和盾牌,像对付敌人一样衝过来的。”
“我亲眼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没了双腿的老伙计,举著他仅剩的荣誉勋章,想对警官说话……被一警棍连人带轮椅打翻在地。马匹从他的践踏过去了……他们甚至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警棍,水龙,还有……枪,有什么他们就用什么。” 勒费弗尔闭上眼,
“我旁边一个来自南特的小伙子,才二十出头,没上过战场,肚子上挨了一下,血怎么也止不住……他倒在我怀里,眼神那么迷茫……,他就那么死了,死在巴黎的街道上,死在他以为保护他的共和国警察手里。”
“那之后,我明白了。这个共和国,它的议会、它的法律、它的警察,保护的不是我们这些流血的、干活的人。
它保护的是银行,是工厂主,是那些让我们去送死、然后在我们残废失业时一脚踢开的体面人。 我们的血,只是他们帐簿上一笔划掉的成本;我们的命,还不如证券交易所里一个跳动的数字。”
“我像野狗一样在巴黎游荡,带著伤,带著恨,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然后,我在塞纳河左岸的旧书摊上,花最后的钱,买到了一本皱巴巴、被禁的小册子。
是从德国翻译过来的,作者叫卡尔·韦格纳。
书名叫《谁该为战爭负责?以及劳动者如何真正拥有未来》。”
勒费弗尔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带上了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那本书里没有空话。它拆解了战爭是怎么发生的——不是因为我们和德国工人有什么仇,而是因为两边的资本家、皇帝、將军们需要爭夺市场、资源和殖民地。
它说,我们士兵在战壕里互相廝杀,不过是替那些从不露面的人当炮灰。
它说,真正的敌人不在对面战壕,而在我们身后的宫殿、银行和议会里。”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清晰地指出了一条路:
劳动者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不是祈求,而是夺取——夺取生產工具,夺取政权,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自己管理、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愚蠢战爭的新社会。
它讲了德国那边的工人是怎么做的,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正在建设。
那本书里的道理,像闪电一样劈开了我脑子里所有的疑问。
我突然明白了,我过去的痛苦、战友的死、街头的鲜血,都不是偶然的倒霉,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谋杀。
而打破这个系统,不仅是报仇,更是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为將来不再有孩子经歷战壕和街头屠杀,找到的唯一出路。”
“我带著那本小册子,找到了本地的工会,后来接触了法共的同志。
一开始,我也警惕,但他们的同志跟我一样是工人,是退伍兵,他们理解我的伤疤和愤怒,但他们不只有愤怒,他们有组织,有学习,有行动计划。
他们教我学理论,分析社会。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遍及全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战壕对面的德国工人。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
我开始参加活动,从散发传单到组织罢工,从学习到在集会上发言。这道疤,”他摸了摸脸上的伤痕,
“不再是耻辱或痛苦的记號,它成了我的勋章——旧世界罪恶的活证据,和为新世界战斗的宣言。”
亨利站起身,
“现在,我站在这里,不是乞求,不是等待被拯救。我和我的同志们,在建设,在守卫,在学习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的街区。
我们知道南边政府区的那些老爷们恨不得把我们碾碎,也知道前路艰难。
但这一次,我们手里有武器。
我们也许还会流血,但再也不会白白流血。每一次斗爭,无论成败,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奠基。”
勒费弗尔的故事讲完了。
他拍了拍斯诺的肩膀,力道很重:
“记者先生,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告诉美国人,告诉全世界还在受苦和迷茫的人:
等待资本家的仁慈,不如等待石头开花。出路不在选票箱里,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在组织起来、认清敌人、並下定决心改变一切的劳动中。”
说完,他转身回到检查点,继续他日常的工作。
当晚,斯诺在左岸一家廉价的旅店房间里,面对著他的打字机和笔记本,久久无法落笔。
白天两个男人的面孔在他脑海中交替浮现:
那个深陷於过去“体面”的幻觉、被资本泡沫榨乾后又因阶级隔阂而自我囚禁的破產律师;
那个被旧国家背叛、在绝望中找到全新阶级认同和战斗意义的老兵。
这是资本主义危机下,同一座城市里诞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悲剧与觉醒。
乞丐的悲剧在於,他曾是那个体系的受益者或自以为是的参与者,以至於当体系崩溃將他吞噬时,他无法在精神上斩断与它的联繫。
他的体面成了他接受救济的障碍,他过去的阶级立场成了他寻求生路的心理枷锁。
他代表了那样一批中產阶级:
他们的世界观与现存秩序绑定得太深,以至於秩序的崩溃也意味著他们个人意义的彻底湮灭。
他们可能饿死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也无法向新生的、带著他们过去对立面印记的曙光迈出一步。
而老兵的觉醒则表明,对於从未在旧秩序中真正拥有过什么、反而被其残酷剥夺和背叛的无產者而言,转向一种彻底批判並意图推翻该秩序的思想,是逻辑的必然,甚至是生存的必需。
他的痛苦是整个阶级被系统性牺牲的缩影。
韦格纳的思想以及更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为他提供的,不仅是对痛苦的解释,更是一个清晰的敌人画像、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蓝图,以及一种將个人苦难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路径,一种赋予伤痕以新意义的敘事。
他从一个被遗弃的、绝望的个体,转变为一个有归属、有目標、正在参与创造歷史的集体中的一员。
斯诺在笔记上写下:
“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產生经济难民,更在大量製造其自身的革命者。
前者被困於旧世界,后者则在废墟上锻造新世界的武器。这是一种比经济需求更深刻、更强大的动力。”
斯诺也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或许正在德国以更系统、更成功的方式上演。而
法国的故事,则展现了这条道路在资本主义腹地斗爭的残酷性、复杂性和未完成性。
合上笔记本,斯诺望向窗外巴黎的夜空。这座城市被无形的界线分割,一边是缓慢腐朽的绝望,一边是艰难孕育的希望。
第341章 一个老兵的故事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