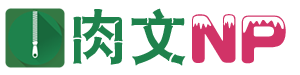轰隆——!
一道炸雷,像是要把这海岛的天灵盖给掀开。
林秀莲猛地从噩梦中惊醒。
“建军!”
她喊了一声,声音却哑得像破风箱。
伸手一摸,身边是冰凉的竹蓆,没有那个火热结实的胸膛。
只有窗外狂风撞击窗欞的“咣咣”声,那是颱风登陆的嘶吼,每一声都像是砸在她心口上。
肚子。
一阵尖锐的坠痛感突然袭来,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肚皮里狠狠抓了一把。
林秀莲脸色瞬间惨白,额头上的冷汗大颗大颗地往下滚。
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身后。
湿的。
虽然不多,但那种黏腻温热的感觉,让她这个做过护士的资本家小姐,瞬间如坠冰窟。
见红了。
恐惧,铺天盖地而来。
建军生死未卜,要是孩子再没了……
“爸……爸……”
她想喊,可喉咙被恐惧堵死,发出的声音比蚊子叫还轻。
吱呀——
那扇贴著“福”字的木门,被轻轻推开了。
没有风灌进来。
因为有一个高大如山的黑影,严严实实地堵在了门口,挡住了身后狂暴的风雨。
陈大炮手里端著一个还在冒著热气的大瓷碗。
煤油灯昏黄的光,打在他那张布满胡茬、如同岩石般坚硬的脸上。
那一双眼睛,全是红血丝,却亮得嚇人。
他鼻子抽动了一下,眼神瞬间锁定了林秀莲捂著肚子的手。
“见红了?”
声音低沉,冷静得不像个活人。
林秀莲哆嗦著点头,眼泪决堤而出:“爸……我怕……孩子……”
陈大炮没说话。
他把碗放在床头的木凳上,大步走过来。
那只满是老茧的大手,没有丝毫犹豫,隔著薄被,稳稳地按在了林秀莲的小腹上。
一股温热、粗糙却无比厚实的力量,透过被子传了进来。
“別动。”
陈大炮另一只手迅速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展开,是一排长短不一的银针。
那是他在老连队跟军医学的保命手艺,专治急火攻心、气血逆乱。
刷刷刷。
三针下去。
足三里、內关、太冲。
行针稳、准、狠。
林秀莲只觉得一阵酸麻感游走全身,那股一直往下拉扯的坠痛感,竟然奇蹟般地止住了。
“气血上涌,惊悸伤肝。”
陈大炮收了针,那张紧绷的黑脸並没有放鬆分毫。
他转身端起那个大海碗。
一股子浓郁醇厚的鱼香味,瞬间在这个充满药味和霉味的房间里炸开。
那是昨晚那条龙躉石斑鱼,只取了最嫩的鱼腹肉,熬了足足三个小时。
汤色奶白,浓得能掛住勺子。
没有放葱姜,只放了一点陈皮和胡椒去腥暖胃。
“喝了。”
陈大炮舀起一勺,吹了吹,递到林秀莲嘴边。
林秀莲偏过头,紧闭著嘴,眼泪顺著眼角流进耳朵里。
她哪吃得下?
只要一闭眼,就是建军在海浪里挣扎的样子,满脑子都是那些“船毁人亡”的鬼话。
“我不吃……我吃不下……”
林秀莲哭著推开勺子,鱼汤洒了几滴在被面上。
“啪!”
陈大炮把勺子重重扔回碗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他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那个小马扎在他两百斤的身躯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吱扭声。
“林秀莲。”
这还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儿媳妇。
声音不再刻意压低,而是带著一股子硝烟味,那是他在战场上训斥逃兵的语气。
“你是不是觉得,建军回不来了?”
林秀莲浑身一颤,哭声噎在喉咙里,惊恐地看著公公。
陈大炮那双眼睛,死死盯著她,像是要把她的灵魂看穿。
“我告诉你,我陈大炮的种,没那么容易死!”
“当年在猫耳洞,老子肠子流出来塞回去还能再杀两个来回!他陈建军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这点风浪算个球!”
“他在前线跟老天爷搏命,想回来见老婆孩子。”
“你呢?”
陈大炮指著林秀莲的肚子,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你就在这绝食?你就在这哭丧?”
“你是想让他回来看到两具尸体?还是想让他就算活著爬回来,也因为没了后,一辈子活在悔恨里?”
这话太重了。
重得像是一把锤子,把林秀莲那颗脆弱的心砸得粉碎,又强行拼凑起来。
“这碗汤,不是给你喝的。”
陈大炮重新拿起勺子,舀起满满一勺乳白色的鱼汤,再次递了过去。
手,稳如磐石。
“这是给我孙子喝的,是给陈家的根喝的。”
“你就是个容器,你也得给我把这油加满了!”
“喝!”
最后这一个字,是命令。
是不容置疑的军令。
林秀莲看著公公那张凶神恶煞却又掩饰不住焦急的脸。
看著那碗熬得浓白的鱼汤——那是公公在颱风来临前,冒著命去海里叉回来的。
她颤抖著张开嘴。
一口。
鲜。
滚烫的汤汁顺著喉咙滑下去,像是给冰冷的身体注入了一股岩浆。
眼泪混著鱼汤一起吞进肚子里。
两口。
三口。
陈大炮就这么一勺一勺地餵。
动作机械,却又透著股笨拙的小心。
直到一碗汤见底,连碗底的鱼肉渣都被餵了进去。
林秀莲的脸上,终於泛起了一丝血色。
那是活人的顏色。
陈大炮长出了一口气,那紧绷的肩膀微微塌下来一寸。
他把空碗放在桌上,那是“完成任务”的信號。
“睡。”
他站起身,替林秀莲掖了掖被角。
动作粗鲁,把林秀莲裹得像个粽子。
“爸……你去哪?”
林秀莲伸出手,像是溺水的人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她怕。
怕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樑柱也消失在风雨里。
陈大炮停下脚步。
他没有回头,只是背对著儿媳妇,从腰间抽出那根旱菸杆,却没有点火。
“我不走。”
他走到门口,把那张平日里自己坐的小马扎搬了过来。
就放在门槛內侧,正对著那扇在风雨中飘摇的木门。
然后。
一屁股坐下。
双腿分开,双手拄著膝盖,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一尊黑铁铸造的门神。
老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钻了出来,抖了抖身上的毛,无声地趴在陈大炮的脚边,把下巴搁在他的军胶鞋上。
一人,一狗。
如果不看那个背景,这就像是一幅静止的油画。
“睡吧。”
陈大炮的声音从门口传来,闷闷的,却带著一种奇异的迴响。
“外头就算是天塌了,有老子在这顶著。”
“风吹不进来,鬼也进不来。”
“你要做的,就是护好肚子里的肉。其他的,交给我。”
林秀莲看著那个宽阔如山的背影。
那是挡在她和死亡、恐惧、绝望之间的一道墙。
眼泪再次流了出来,但这一次,不是因为怕,是因为安。
她闭上眼,那股子鱼汤的热气在胃里翻腾,化作了困意。
……
这一夜,极其漫长。
外面的颱风像是发了疯的野兽,撕扯著海岛上的一切。
屋顶的瓦片被掀飞了几块,发出噼里啪啦的碎裂声。
院子里的那棵老歪脖子树,被连根拔起,重重砸在陈大炮砌的那圈刺槐篱笆上。
但陈大炮纹丝不动。
他就像是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这门口。
他没有睡。
他在听。
听风声,听雨声,听海浪拍击岸边的声音。
也在听屋里儿媳妇的呼吸声。
每一次呼吸平稳,他手里摩挲菸斗的动作就会慢一拍。
每一次呼吸急促,他的肌肉就会瞬间紧绷。
记忆像是潮水一样涌上来。
上辈子,也是这样的雨夜。
他在老家,抱著收音机,听著外面的雨声,心却冷得像铁。
那时候他还在恨,恨儿媳妇娇气,恨儿子不听话。
结果呢?
等到的是那一通报丧的电话。
那一夜,他没守住家。
这一世。
陈大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那双杀过猪、杀过敌、如今又学会了给儿媳妇熬汤的大手。
“贼老天。”
他在心里默念,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弧度。
“你想收人?问过老子手里的刀没?”
……
不知道过了多久。
风,似乎小了些。
窗户纸透进了一丝灰濛濛的光。
天亮了。
颱风眼过境,暂时的寧静笼罩了整个家属院。
但这寧静比风暴更让人窒息。
因为这意味著,结果要出来了。
“吱——”
陈家小院那扇被风吹得半掉的院门,被人推开了。
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是隔壁的刘红梅,还有几个平日里爱嚼舌根的军嫂。
她们不是来帮忙的。
她们是来看戏的。
或者是来印证那个“陈连长已经餵鱼了”的谣言的。
刘红梅吊著胳膊,探头探脑,脸上带著一种令人作呕的悲悯和窃喜。
“哎哟,这屋顶都掀了,也不知道秀莲那丫头嚇流產没……”
话音未落。
堂屋的门,开了。
陈大炮走了出来。
他在门口坐了一整夜,身上带著一股子浓重的寒气和潮气。
眼窝深陷,胡茬冒出来一圈,青惨惨的。
但那股子精气神,却比昨晚还要嚇人。
他手里提著那根昨晚没点燃的旱菸杆,另一只手,牵著老黑。
他就那么往门口一站。
没有说话。
仅仅是一个眼神。
那种在死人堆里滚过、此刻又处於爆发边缘的眼神。
刘红梅到了嘴边的閒话,硬生生给咽了回去,像是吞了一只苍蝇。
她感觉自己被一头饿虎盯上了。
只要她敢再说一个字,这老头绝对会扑上来咬断她的喉咙。
“滚。”
陈大炮嘴唇动了动。
声音不大,沙哑,乾裂。
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带著血。
“靠近院子三米,腿打断。”
刘红梅等人浑身一抖,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她们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甚至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清理完这些苍蝇。
陈大炮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紧闭的房门。
里面,林秀莲的呼吸声平稳。
还好。
守住了。
他抬头,看向远处依旧阴沉的海面。
海浪还是很大,灰黑色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拍打著码头。
没有船回来的跡象。
也没有搜救队的消息。
第20章 只要老子还有一口气,这天就塌不下来!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