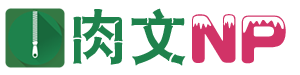第5章:贾后警觉,宫防加固如铁桶
天快亮了,宫城里还黑著。远处传来一声鸡叫,短促而哑,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喉咙。
贾南风坐在椒房殿內,手里握著一柄玉如意,指尖来回摩挲著上面的纹路。她没睡。昨夜翻来覆去,总觉心口发闷,像有东西压著。窗外风不大,可烛火偏生一跳一跳的,照得墙上人影晃动,仿佛有人在暗处窥视。
她盯著那影子看了半晌,忽然开口:“外头谁当值?”
帘外立刻有人应声:“回娘娘,是侍卫统领陈安,在殿外候著。”
“叫他进来。”
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穿深褐甲衣的中年汉子低头跨过门槛,单膝跪地:“属下参见皇后。”
贾南风没抬头,依旧把玩著手里的玉如意,声音不高:“这几日宫里可有什么异样?”
陈安顿了一下:“一切如常。各门巡更照旧,未见疏漏。昨夜三更后闭了西掖门,东华门也加了双哨,按例行事。”
“按例?”她冷笑了一声,“我问你,司马伦府上的人进出可查过?”
“这……”陈安迟疑,“按宫规,宗室府邸不在日常稽查之列。除非有詔令,否则不便擅自盘问。”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她抬眼盯住他,“你当我不知道?春社日那天,他请我赴宴,嘴上说得恭敬,眼神却稳得很。那种人,能安什么好心?”
陈安低著头,额角渗出一层细汗。
“我不是要你现在就抓人。”她语气缓了些,“我要的是防。从今日起,司马伦府每日出入几人、何时出门、往哪个方向走,都要记下来。他若派人去城外,立刻报我。还有,他府上的门客,凡是见过两回以上的,都给我画像存档。”
“是。”陈安应下,但没动身。
“怎么?”
“属下只是想问……若他察觉我们在盯他,会不会反咬一口,说我们构陷宗亲?毕竟他是赵王,又是先帝叔辈,名分上……”
“名分?”她猛地將玉如意往案上一磕,发出“啪”一声响,“太子是什么名分?国本!他一句话就想废就废?如今连个审讯都没有,直接贬去许昌。你们还跟我讲名分?”
陈安不敢再言。
她盯著他,声音压低:“我知道你在怕什么。无非是怕担责。可你要想清楚——我是皇后,掌宫政。现在宫里我说了算。你听我的命令,出了事我扛;你不听,回头出了乱子,你全家都得陪葬。”
陈安脊背一凉,连忙叩首:“属下明白。即刻安排人手,严密监视赵王府动静。”
“不止是他。”她摆摆手,“所有与他往来密切的宗室,齐王、成都王那边也要留意。尤其是夜间往来,一只鸟飞过去都得给我盯住了。”
“是。”
“去吧。”
陈安退出殿外,脚步匆匆。不到半个时辰,宫中各门禁便悄然变了模样。
南宫门依旧开著,但进宫的官员发现,守门侍卫多了两倍,每人腰间佩刀都解了下来,由宦官逐一查验身份文书。没有提前三日报备的,一律不得入內。苍龙巷原本是宗室车马通行的便道,如今被铁链拦起,只留一条窄缝,供两人並行通过。夜里更是连灯笼都不许点,说是“以防贼火”。
御马监那边,马匹清点频次由每日一次改为三次,凡无令牌调马者,立时拘押。兵器库加派了四名宿卫,钥匙由两名宦官分別保管,取用需双签画押。就连平日送菜的厨役,进宫前也要脱鞋搜身,连菜筐底都要翻过来检查。
到了下午,一道新令传遍六率宿卫:自即日起,三班轮换制改为两班急巡,每班缩短为三个时辰,確保全天候警戒不鬆懈。各宫门增设暗哨,藏於廊柱之后、屋檐之上,专盯可疑之人。夜间除中阳门保留通行外,其余偏门一律落锁,无符节不得开启。
一名老宦官捧著黄绢走进椒房殿,低声稟报:“娘娘,《宫禁七条》已誊抄完毕,正送往各司张贴。”
贾南风接过一看,逐条念出:
“一、五品以下官员入宫,须提前三日报备姓名、事由、隨从人数;
二、宗室成员非奉詔不得接近宫墙三百步內;
三、赵王司马伦府每日动向须专报;
四、夜间巡更不得少於八趟,每趟间隔不得超过一个时辰;
五、任何私传书信、密会宫人者,以谋逆论处;
六、宫中奴婢不得擅自与外臣府邸通信;
七、凡发现异常,即时上报,瞒报者同罪。”
她看完,点了点头:“贴去各门、各署,一个都不能漏。尤其是尚书台和门下省,给我盯紧了那些成天写奏章的文官。”
老宦官应声退下。
殿內重归安静。她靠在榻上,闭目养神,可眼皮底下仍在跳动。她知道,这些措施已经超出寻常宫规太多。以往惠帝在时,宫禁宽鬆,连大臣都能带剑上殿。如今突然收紧,必有人背后议论她是多疑暴虐。可她不在乎。
她比谁都清楚,有些事,不是等证据齐全才动手的。等你看见刀子,脖子早就断了。
她睁开眼,唤道:“来人。”
帘子掀开,一名身穿灰袍的中年宦官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跪坐在地,不发一语。
这是她最信任的心腹,姓刘,自幼服侍她,从洛阳东宫一路跟到今日,嘴巴严,手脚利索,从不出错。
“你觉得,司马伦会做什么?”她问。
刘宦官低头道:“依奴婢看,他不会轻举妄动。六十多岁的人,又无兵权在手,若真要反,早就在废太子时动手了。可他没。反倒在朝会上替太子说话,博了个忠义名声。”
“可正是这样才可怕。”她缓缓道,“他越是沉得住气,越说明他在等。等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时机。”
“那……要不要先下手?”
“杀他?”她摇头,“不行。他是赵王,又是宗室长辈。无罪诛杀,天下不服。就算我下令,禁军也不一定肯动。更何况,杀了他,反倒给了別人起兵的藉口。”
她停顿片刻,忽然问:“有没有法子,让他自己犯错?”
刘宦官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道:“或许……可以设局。比如,放出风声说废太子旧部正在联络他,图谋迎立。他若慌了神,派人去许昌探信,或是私会旧臣,便是破绽。”
她眼睛一亮:“对。不能我们动手,得让他自己跳出来。”
“只是……”刘宦官犹豫,“若他根本不理呢?稳坐府中,装聋作哑,我们也没办法。”
“那就逼他出招。”她冷笑,“明日就派两个人,扮作江湖术士,去他府外算卦,说什么『龙困浅滩,终有腾云之日』『废储未绝,血亲尚存』之类的话。他若不动心,也就罢了;若派人来抓,说明他在意;若放任不管,反倒可疑。”
“还可散布谣言。”刘宦官接话,“就说『赵王欲联齐王,共扶太子还朝』。这话传到其他藩王耳中,他们必生忌惮。有人会告发,也有人会观望。只要他身边有人动摇,消息迟早会漏出来。”
她点头:“就这么办。你亲自去安排。找几个嘴碎的宦官,往宗室府邸走动,故意提起这事。再让城南那个说书的老头,在茶馆里讲一段『忠臣救主』的故事,影射司马伦。”
“是。”
“还有,立刻遣人往许昌。”她压低声音,“查太子现在何处,身边有哪些人进出。若发现有人打著司马伦的旗號去见太子,马上回报。”
“若真有其事呢?”
“那就是天赐良机。”她嘴角微扬,“到时候,我不光能除他,还能顺手清理一批跟他走得近的宗室。这一局,要么不动,要动就得斩草除根。”
刘宦官低头称是,却没有立刻起身。
“还有什么?”她问。
“奴婢只是想提醒一句……眼下宫防虽严,可终究是防內。若是外头有人呼应,比如地方上的刺史、太守突然带兵入京,咱们一时也挡不住。”
“所以更要快。”她站起身,在殿中踱了几步,“我不要万全,我要的是在他还没准备好之前,先把他的路堵死。只要他一动,我就有理由动手。”
她停下脚步,望向窗外。
天色阴沉,云层低垂,像是要下雨,却又迟迟不下。
“他以为我不敢动他。”她轻声说,“可他忘了,我能废太子,就能废任何人。他不过是个老王爷,手里没兵,朝中无党,凭什么跟我斗?”
“但他有名义。”刘宦官低声提醒,“清君侧、復储位,这种话一旦传开,民心易动。”
“民心?”她嗤笑,“百姓只知道谁给饭吃。现在米价稳定,京城无乱,谁会为了一个被废的太子上街拼命?真正要紧的,是那些穿紫袍、戴金印的人。只要他们不动,天下就乱不了。”
她转身坐下,重新拿起玉如意,轻轻敲著案几。
“去办吧。记住,所有事都要隱秘。不准用宫中正式文书,不准留字据。一切口头传达,事后不留痕跡。”
“是。”
刘宦官退出殿外,脚步轻得像猫。
殿內只剩她一人。
她把玉如意放在腿上,双手交叠,双目微闭,看似镇定,实则心绪翻涌。
她知道,从今天起,宫里已经不一样了。巡逻的脚步声更密了,守卫的眼神更警惕了,连空气都变得紧绷。可她也知道,这一切还不够。
真正的风暴还没来。
她只是提前把桶箍紧了些。
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是新的当值宦官来换岗。她没睁眼,只听见那人屏息走近,低声稟报:“启稟娘娘,西华门方才截住一名小吏,自称是赵王府送来递帖子的,却被查出袖中藏有一封密函,尚未拆封。”
她这才缓缓睁眼:“密函呢?”
“已被当场扣下,现由陈统领亲自看管,等候娘娘示下。”
“拿进来。”
宦官迟疑:“陈统领说……未经查验,恐有危险,不如当场焚毁。”
“我说拿进来。”她声音不高,却带著不容置疑。
片刻后,一封用蜡封好的竹筒被呈上。她接过,手指在蜡封上轻轻一抹——没动。她没让人拆,也没自己动手。
“放著吧。”她说,“等我亲自看过。”
宦官退下。
她盯著那竹筒看了很久,最终把它放在案角,离自己不远不近。
然后,她重新闭上眼,手搭在玉如意上,一动不动。
殿外,巡逻的靴声来回不断,像雨点打在瓦上。
宫墙之內,铁桶已成。
可桶外的人,还在等风。
第5章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