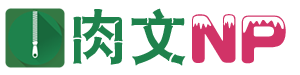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转眼间,又是一年深秋。
京城的风,带著萧瑟的凉意,捲起满地金黄的落叶,也吹走了四合院里,最后一丝残存的、属於旧时代的喧囂。
这风仿佛带著某种意志,要將一切过往的痕跡都刮擦乾净,只留下一个崭新而冰冷的骨架。
这一天,一个瘦削、佝僂的身影,背著一个洗得发白、边角磨损的破旧帆布包,出现在了四合院那熟悉的垂花门前。
是傻柱。
一年,仅仅一年的劳动改造,便像一把最无情、最精巧的刻刀,在他身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这把刀剔去了他所有的血气和稜角,只留下一个顺从的、被掏空了的驱壳。
他的皮肤,不再是那个在后厨烟火中熏出的、带著油光的健康色泽,而是被常年的烈日和风霜侵蚀得黝黑粗糙,像一块饱经风雨的陈年树皮。
他的双手,曾经能顛动沉重的大铁勺,能切出薄如蝉翼的肉片,如今却布满了厚得像盔甲的老茧和一道道深可见肉的裂口。那双手在秋风中微微颤抖著,不再是为了炫技,而是因为长久劳作后留下的神经损伤。
最可怕的变化,在他的眼神里。
那双曾几何时盛满了“浑不吝”的悍勇与生机的眼睛,早已没了光彩。如今,那是一对浑浊、麻木的眼珠,像一潭被无数根棍子搅动了千百次后,终於放弃了挣扎、彻底沉淀下来的死水。再也泛不起半点波澜,无论是愤怒、是喜悦,还是悲伤。
他回来了。
回到这个承载了他前半生所有荣辱、交织了全部爱恨的地方。
他站在院门口,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他看著眼前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院子,一时间,竟有些恍如隔世。记忆中的画面如同褪色的老旧电影胶片,与眼前清晰而冷酷的现实交叠在一起,產生了巨大的割裂感。
院子,变了。
变得乾净了,整洁了,也变得……死气沉沉了。
记忆中那条下雨就泥泞不堪、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坑洼土路,被平整、光滑、泛著清冷白光的水泥地所取代。走在上面,脚步声都显得格外清晰和孤独。
墙角下那些堆放著破桌烂椅、废旧煤球的杂物堆,也都不见了踪影,清理得乾乾净净,仿佛这里从未有过生活的凌乱痕跡。
只有那棵冠盖了整个院落的老槐树,还像以前一样,执拗地矗立在原地。只是此刻,它也早已褪尽了一身繁华,在萧瑟的秋风中,无声地摇曳著光禿禿的、如同嶙峋怪手的枝丫,在灰白的天空下勾勒出几笔苍凉的剪影。
院里很安静,一种 unnatural 的安静。
没有了孩子们的吵闹声,没有了夫妻间的爭执声,更没有了他年轻时,一进院门便扯著嗓子与人斗嘴的喧譁。
几个大妈正坐在新砌的墙根下,沐浴著深秋午后那点可怜的、没有温度的阳光。她们手里不停地纳著鞋底,针线穿梭间,嘴唇也在翕动著,小声地聊著东家长西家短。
她们的目光,几乎是同时,落在了傻柱的身上。
先是一愣,仿佛在辨认这个形容枯槁的人究竟是谁。
当辨认清楚后,那几双眼睛里,几乎是瞬间,便同时流露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却又高度统一的情绪——有那么一丝丝如同看待路边流浪猫狗的同情,有那么一点点源於道德优越感的鄙夷,但更多的,是一种刻意的、生怕沾染上晦气的疏远。
就像看到了一件不祥之物,她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原本的交谈声也戛然而止。其中一个甚至下意识地拉了拉身边人的衣角,几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齐齐地低下了头,假装专注於手里的针线活,再也不看他一眼。
没有人跟他打招呼。
没有人问他一句“回来了?”
仿佛他只是一个透明的、不存在的幽灵。
傻柱也习惯了。
在那个地方,他早已学会了如何將自己视作无物。他低下头,用帽檐遮住自己那双空洞的眼睛,默默地,一步一步,走进了这个曾经被称为“家”的院子。
他先是下意识地,几乎是出於一种动物本能的畏惧,朝著后院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个曾经让他又敬又怕,时而如天神般威严、时而如恶魔般可怖的男人的屋子,窗户紧闭,门前落满了枯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夜晚亮过温暖的、或是在他看来是审判的灯光了。
他零星地听说了一些。
那个名叫何援朝的男人,他名义上的“弟弟”,这个院子真正的君王,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干一件天大的、他连想像都无法触及的事情了。
他走了。
但他的传说,他的威严,他定下的规矩,却像一道无形的、密不透风的结界,依旧牢牢地笼罩著这个院子里的每一个人。这结界过滤掉了所有的杂音和混乱,也抽走了所有的生气和人情味,让所有人都屏息凝神,规规矩矩地活著,连大声喘气都成了一种奢侈。
傻柱收回目光,那目光里没有怀念,只有深入骨髓的恐惧。他又机械地,转向了中院。
贾家的屋门,同样紧紧地闭著。
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沉的木色。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一丝生气,不像当年,总是围满了人,或是等著秦淮茹周济,或是看著他们家上演的一出出闹剧。
关於贾家的消息,在他改造期间,也像风一样,断断续续地飘进过他的耳朵。
他听说,秦淮茹的病,时好时坏,被生活和心病反覆折磨,人已经彻底垮了,再也不见当年的半分风韵。
他还听说,贾张氏,在经歷了儿子惨死、孙子入狱、家庭分崩离析的一系列打击后,精神彻底失常,成了一个只会日夜不停咒骂的疯婆子。
这个曾经是他生命中最重要坐標的家,如今,已经名存实亡。
他以为自己会痛,会难过,会有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意。
但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的心里,平静得像他眼里的那潭死水,竟没有泛起半分波澜。
那些曾经让他魂牵梦縈、掏心掏肺、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过往;那些为了一句软语、一个微笑就让他心甘情愿付出的岁月;那些深更半夜为她家留下的饭菜,那些替她家出头而挥舞的拳头……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年繁重到磨灭人性的体力劳动和无尽悔恨的自我鞭笞里,早已被磨得一乾二净,连一点点残渣都没有剩下。
他现在,只想活著。
像条狗一样,不需要尊严,不需要理想,甚至不需要情感。只要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遮风避雨的角落,安安静静地,活著。
他拖著沉重的脚步,终於走回了自己那间位於前院的小屋。
门上掛著一把已经锈跡斑斑的锁。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那把冰冷的钥匙,有些笨拙地,捅了半天才对准锁孔。
“嘎吱——”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后,门被推开了。
一股混杂著灰尘、潮湿和腐败的陈腐气息,扑面而来,呛得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屋里光线昏暗,目之所及,一切都覆盖著厚厚的一层灰尘。桌上,床上,灶台上,像被降下了一场经年不化的灰色的雪。角落里,蜘蛛网结得肆无忌惮,昭示著这里被遗弃了多久。
他默默地放下帆布包,没有丝毫的伤感,只是开始动手收拾。
他找来扫帚,一点点地將地上的灰尘与落叶扫出。每一个动作都显得缓慢而机械。
他用袖子擦去桌上的尘土,看著桌面慢慢显露出原本的木纹。
他走到灶台前,看著那口早已生锈的铁锅,锅底还残留著一年前最后一次做饭后留下的黑色印记。他拿起锅,走到水缸边,舀起冰冷的清水,开始费力地清洗著。铁锈的腥味,瀰漫在空气里。
他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执行著脑中既定的程序。
就在这时,“咚咚咚”,门,被敲响了。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傻柱的身体猛地一僵,手中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缓缓转过身,看著门口那个逆著光的身影。
是街道办的王主任。一个总是穿著中山装,戴著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的中年男人。
王主任看著眼前这个几乎变了模样的何雨柱,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agis的嘆息,但很快就被公式化的严肃所取代。他推了推眼镜,从隨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摺叠得整整齐齐的文件。
“何雨柱同志。”
王主任的语气,公事公办,听不出任何个人情绪。
“你回来了,就要重新开始生活。这是轧钢厂对你的最新工作安排,你看看。”
傻柱茫然地伸出那只还在滴著锈水的手,在裤子上胡乱擦了两下,才有些迟疑地接过了那份文件。
“根据何援朝同志离开北京之前的特別嘱咐,以及厂领导班子的集体研究决定,”王主任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敲进傻柱的耳朵里,“从明天起,你,就去厂里的三號仓库,当一名仓库保管员。”
他顿了顿,似乎是在给傻柱消化信息的时间,然后继续用那种平淡无波的语调补充道:
“工作不累,主要是登记和看管货物,但要认真负责,不能出差错。工资方面,暂时按学徒工的標准发放。你先干著,好好表现,端正態度,以后……也许还有转正的机会。”
仓库保管员?
学徒工的工资?
傻柱拿著那份薄薄的、却足以决定他下半生命运的文件,手,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
他低头看著纸上的铅字,那一个个黑色的方块字,在他的眼中开始扭曲、跳动,最后匯成了一张巨大而无情的网。
这张网,是何援朝,为他精心编织的。
他知道,这是那个男人,对他最后的“仁慈”。
也是,对他最后的“掌控”。
给了他一个铁饭碗,一个在厂里的正式编制,让他不至於流落街头,饿死冻死。让他能活下去。
却也把他,像一枚生了锈的图钉,死死地钉在了一个最底层、最没有前途、永远也翻不了身的位置上。
一个曾经名震京城的大厨,如今只能去看守冰冷的仓库。一个曾经月薪九十九块的八级工,如今只能拿那点可怜的学徒工工资。
这比杀了他,更让他感到屈辱。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永无止境的凌迟。
让他,一辈子,都得仰仗这份“恩赐”过活。
让他,这一辈子,都活在他何援朝的阴影之下,时刻谨记著这份“宽恕”,时刻提醒著自己,是谁,主宰著他如今这卑微的命运。
“……谢谢。”
傻柱的嘴唇蠕动了半天,喉咙里像是被塞满了沙子。最终,他只从喉咙深处,挤出了这两个乾涩、嘶哑、连他自己都听不真切的字。
他不知道,自己该谢谁。
谢何援朝的不杀之恩?
还是谢命运这无情而辛辣的嘲弄?
王主任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满意,转身便离开了,留下傻柱一个人,呆立在满是灰尘的、冰冷的屋子里。
……
第二天,傻柱换上了一身不算合身但还算乾净的工装,准时去三號仓库报到了。
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页……充满了灰色和麻木的、再也看不到半分光亮的新篇章。仓库里阴冷潮湿,堆满了各种散发著机油和铁锈味的零件。他的工作就是拿著本子,核对来往的货物,然后在冰冷的货架间穿梭。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傍晚,下班的铃声响起。
他领到了第一天的工钱——三角五分。
他用那双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捏著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感觉到一种荒谬的刺痛。三角五分,曾几何时,这连他请客吃饭时掉在地上都懒得去捡的零钱,如今,是他一天劳动的全部价值。
他捏著钱,在厂门口的小卖部里犹豫了许久。最终,他买了一瓶最便宜的二锅头,和两个冷得像石头一样的窝头。
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双脚不听使唤,鬼使神差地,一步步,又走到了中院,走到了贾家的门口。
那是一种病態的惯性,像一头被驯养多年的老马,即使挣脱了韁绳,也依然会沿著旧路回到马厩。他只是想去看看,去看那片废墟,以確认自己內心的坟墓也同样牢固。
屋里,隱约传出贾张氏那顛三倒四、毫无逻辑的疯癲咒骂声,夹杂著棒梗愈发暴躁不耐烦的吼叫:“你他妈有完没完!再吵老子弄死你!”
这声音,让傻柱的脚步顿住了。
就在此刻,门,“吱呀”一声,突然从里面被拉开了。
是秦淮茹。
她端著一个空空的药碗走出来,似乎是想去倒掉。
她比一年前,在傻柱记忆中的最后印象里,更老了,也更瘦了。岁月和病痛,像两把无情的銼刀,磨去了她脸上所有的光华和血色。
头髮已经花白了大半,凌乱地挽在脑后。眼神浑浊不堪,再也没有了当年勾人心魄的波光。脸上,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绝望,仿佛灵魂已经被抽乾,只剩下一具被生活反覆蹂躪的躯壳。
两人四目相对。
隔著不到两米的距离,隔著一年的时光,隔著一道生与死的鸿沟。
没有惊讶,没有欣喜,也没有怨恨。
秦淮茹的脸上,只有一闪而过的茫然,隨即也归於一片死寂。
傻柱的脸上,则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表情。
他们的对视,只有一片……死寂的麻木。
仿佛,只是两个在无边苦海中各自挣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偶然间对上了视线,然后又各自错开。
傻柱看著她,看著这个他曾以为是生命全部意义的女人,沉默了半晌。他看到她乾裂的嘴唇,看到她瘦到脱形的脸颊。
然后,他做了一个连自己都未曾预料的动作。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还带著他微弱体温的窝头,又从口袋里摸索出刚领到的工资,抽出那张崭新的两毛钱的票子,一起递了过去。
他什么话也没说。
这个动作,只是一个残留在他身体记忆深处的、古老的本能。一个餵食者的本能。
秦淮茹看著他手里递过来的东西,那双死水般的浑浊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第一次,泛起了一丝微弱的水光。
但那水光,转瞬即逝。
她没有接。
她只是看了看那窝头,又看了看傻柱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然后,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
那动作,带著一种决绝的、不容置喙的意味。
隨即,她缓缓地,拉上了身后的门。
“哐当。”
一声轻响,將他和这个世界,將她和他之间所有荒唐的过去,都彻底隔绝在了门外。
傻柱看著那扇紧闭的、冰冷的门,片刻之后,嘴角咧开,发出一声自嘲的、比哭还难听的轻笑。
他將那个窝头,轻轻地,放在了门前的石阶上。像是在完成一个最后的、毫无意义的仪式。
然后,他转过身,不再有任何留恋。
他拧开酒瓶的盖子,仰起头,对著瓶口,狠狠地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廉价的酒液,像刀子一样,划过他的喉咙,衝进他的胃里,燃起一团灼热的火焰。那股强烈的刺激,呛得他眼泪都流了出来。
分不清是呛出的泪,还是迟来了一辈子的、为自己而流的泪。
他,和她。
他,和这个院子。
他,和那段他付出了半生去追逐的、荒唐得可笑的梦。
在这一刻,在这一口辛辣的酒里,终於……都结束了。
舔狗的最终章,不是轰轰烈烈的復仇,也不是幡然醒悟的解脱。
而是在看透了所有虚妄之后,那无声的、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活著。
傻柱摇摇晃晃地,走回了自己那间位於前院的、冰冷的小屋。
他不知道,自己这灰暗得看不到一丝光亮的人生,还要持续多久。
也不知道,那个如同神魔般笼罩著他一切的男人,是否还会再回来,再次审视他这卑微的残生。
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的人生,早已在那个人决定他命运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
第115章:院落的最后丝线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