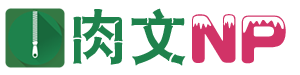墨索里尼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背对著房间里忐忑不安的幕僚们。
“德国人停在了佛罗伦斯城外。
他们在等什么?等我自己走出去,把罗马双手奉上吗?”
房间里,国防部长巴多格里奥元帅、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墨索里尼的女婿)、黑衫军总参谋长卡尔米內·塞尼塞,以及几位內阁部长沉默地站著。
空气里瀰漫著一种微妙的气息,每个人都在算计著,在墨索里尼倒台后,自己该站在哪一边,如何保全性命、財富,还有权力。
“领袖,”
齐亚诺小心翼翼地开口,
“瑞士渠道传来新消息……国王陛下昨天会见了美国大使。谈话內容不详,但会面时间长达三小时。”
“维托里奥?”
墨索里尼转身,
“那个懦夫!他以为美国人能救他?还是以为把我交出去,他就能继续坐在奎里纳莱宫里当他的橡皮图章国王?”
巴多格里奥元帅清了清嗓子:
“领袖,当前军事情势严峻。佛罗伦斯守军士气已濒临崩溃,如果德军强攻,城市可能撑不了多久。
而佛罗伦斯一旦失守,罗马以北將无险可守。”
“所以你的建议是什么,元帅?”
墨索里尼盯著他,
“像北方的那些叛徒一样,升起白旗?”
“我的建议是……考虑政治解决方案。”
“通过中立国,与柏林和意共解放区接触,探討停战条件。
战爭进行到这个阶段,继续抵抗只会让义大利遭受更严重的破坏。”
墨索里尼的拳头重重砸在办公桌上: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我寧可把罗马炸成废墟!”
但当墨索里尼咆哮时,他注意到,一旁的齐亚诺低头玩弄著戒指,塞尼塞的目光游移,几位部长交换著眼神。
没有人响应他的“豪言壮语”。
一种冰冷的寒意顺著墨索里尼的脊椎爬上头顶。
他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可能已经在准备他的后事了。
墨索里尼的记忆闪回:
1914年的米兰,《前进!报》编辑部。
那时的墨索里尼还不是“红色贝尼托”——义大利社会党(psi)《前进!》报的主编。
他当时还在用充满煽动力的嗓音对工人们演讲:
“无產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產阶级国家!
议会斗爭是骗局,罢工是乞討,只有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能带来真正的解放!”
台下掌声雷动。
那时的他真诚地相信这一切。
他读过马克思,钻研过索雷尔的暴力革命论,研究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斗爭经验。
在党內,他被视为激进的“革命派”,与当时更倾向於议会道路的党內主流格格不入。
转折点发生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社会党主流坚持“无產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义大利参战,主张“既不要支持国王,也不要支持皇帝”。
但墨索里尼——出於一种复杂的心態混合:
对“行动”的渴望、对“革命通过战爭加速”的幻想、或许还有对个人影响力的算计——突然在《前进!》报上发表长文:
“在这场帝国主义战爭中保持中立是懦弱!战爭將摧毁旧秩序,为革命创造条件!
义大利应该参战——不是为了国王和资本家,是为了让战爭变成內战的序幕!”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墨索里尼就被社会党开除了。
1915年,墨索里尼自愿参军,想证明自己不是空谈家。
但在伊松佐河前线,他看到的是无意义的屠杀:
义大利农民子弟和奥地利农民子弟在泥泞中互相廝杀著,军官们躲在后方享受特权,资本家靠军火合同赚得盆满钵满。
他本人也被弹片所伤,休养了半年。
战爭没有如墨索里尼所希望的带来革命,只带来了混乱和绝望。
1917年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医院里。最初的墨索里尼兴奋的想著——看,战爭果然催生了革命!
但隨后的消息让墨索里尼感到困惑:列寧与德国单独媾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俄国共產党(布尔什维克)在镇压其他左翼政党,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的“无產阶级专政”。
“这不是我想要的革命。”
“用一个新的专製取代旧的专制,用党的官僚取代资本家的官僚……这算什么解放?”
墨索里尼的思想开始剧烈转向。
如果无產阶级专政最终只是换了一批统治者,如果国际主义在民族仇恨面前不堪一击,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
1918年的米兰街头,11月11日,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像所有人一样鬆了口气——战爭结束了。
但紧隨其后的新闻,却让墨索里尼从椅子上猛地站起:
“德国爆发革命!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
“卡尔·李卜克內西宣布『共和国』诞生!”
“前帝国陆军的韦格纳在304高地起义,整合边境德军开始向柏林进军!”
报纸上的报导一篇比一篇惊人。
起初墨索里尼不以为然:又一场短暂的骚乱罢了,就像俄国的二月革命,很快会被镇压。
但接下来的发展让墨索里尼感到坐立不安:
很快,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在柏林正式宣告成立。
到春天,德国竟然初步稳住了局面,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
墨索里尼捧著报纸的手在抖。
这不可能。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有著根深蒂固的容克贵族和资產阶级,有著严密的官僚体系和军事传统。
按照所有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国家应该是最难革命、革命后也最难维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態的。
可是韦格纳——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人——竟然做到了。
更让墨索里尼焦虑的是德国革命展现出的新型特质:
它强调组织效率和务实建设;它在坚持无產阶级专政的同时,竟然还能维持一定的生產秩序和社会稳定。
社会党朋友寄来的德共宣传品上写著:
“我们不摧毁技术,我们接管技术;我们不消灭知识分子,我们改造知识分子。”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革命……”
墨索里尼在日记里写道,字跡潦草而激动,一旁放在桌子上的《晚邮报》,头版標题上写著:
“柏林红旗飘扬——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详细报导描绘了一个他所嚮往的景象:
工人士兵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土地改革……。
报导特別提到一个名字:卡尔·韦格纳。
“一个军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喃喃自语,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共鸣。
他自己也是从社会党激进派转型(儘管是被开除),也相信暴力革命,也崇拜行动力。
但韦格纳做到了他不敢想的事——在欧洲心臟地带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红色政权。
墨索里尼做了一个决定。他找出1914年被社会党开除时撕碎的党证残片,用颤抖的手给米兰的义大利社会党支部写了一封信:
“同志们,过去几年的迷惘让我付出了代价。如今歷史给出了新的答案——看看柏林吧!那才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应有的形態。我请求重新审查我的立场,我愿意在党的纪律下工作,为义大利的解放贡献力量。”
回信在一周后送达,简短而冰冷:
“本党认为您在1914年的行为不可原谅。您对战爭的支持已证明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另:
您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中仍充斥著民族主义情绪,这与无產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悖。”
他不死心。既然义大利的同志不理解他,那么也许——也许柏林的同志能理解?
2月,他通过瑞士的中间人,向柏林寄去一封长信,收件人直接写了“卡尔·韦格纳同志”。
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德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的钦佩,分享了自己早年对社会党的贡献,甚至暗示愿意“在国际革命事业中扮演角色”。
石沉大海。
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那时的德国还处在忙碌的基础建设和內部整合之中,这封信有没有穿越奥地利抵达德国境內谁也不知道。
“真正的无產阶级先锋……”
墨索里尼苦笑著重复这句话,把信稿扔进壁炉。
火焰吞噬纸张时,他想起了葛兰西——那个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是的,那才是义大利共產党想要的“先锋”,不是他这个有过“污点”的前社会党人。
但墨索里尼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仍未熄灭。
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更疯狂的决定:
亲自去柏林看看。他变卖了几件值钱物品,弄到一份记者证件,准备以採访名义前往德国。他想亲眼看看韦格纳创造的奇蹟,想站在那个让他既嫉妒又崇拜的人面前,亲口问:“你看不出我们其实是同类吗?都是行动者,都是要打破旧世界的人!”
行程定在4月15日。
但4月10日,米兰爆发了警察与失业退伍军人的大规模衝突。作为退伍军人团体里小有名气的鼓动者,他被警方盯上,护照被暂扣“配合调查”。等他摆脱麻烦,已是5月。
而这时,义大利的局势已经天翻地覆——工厂占领运动达到高潮,义大利共產党影响力急剧扩张,墨索里尼的那些退伍军人簇拥天天来找他:
“贝尼托,我们该怎么办?共產党要把工厂都占了!”
他被困住了。一边是未能成行的柏林之旅,一边是义大利沸腾的阶级斗爭。
最终,墨索里尼还是把墙上残存的社会党宣传画全部撕碎。然后坐到桌前,开始起草一份全新的纲领。
標题是:《战斗的义大利法西斯——反对一切旧势力的民族革命宣言》。
“既然红色的大门对我关闭了,”
墨索里尼写著,
“那我就自己开一扇门。一扇更大、更耀眼、只属於我自己的门。”
从那一天起,曾经的“红色贝尼托”彻底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要证明“没有你们,我照样能创造歷史”的墨索里尼。
他的法西斯主义,从此带上了一种深刻的怨念色彩:
他借鑑红色德国的组织技术,却宣称“这是罗马军团传统的现代復兴”。
他模仿无產阶级专政的集中原则,却包装成“领袖与民族的神秘结合”。
他甚至盗用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纲领(反大资本、社会福利),却坚称这是“民族的、非阶级的社会主义”。
埋藏在墨索里尼心里最深层的秘密是: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被红色阵营拒绝的天才(他自认为)的报復性创造。
他要向义大利、向欧洲、向柏林证明:
你们不要我?好,那我就建一个比你们更强大、更受欢迎、更能吸引人民的运动。我要让你们后悔。
回到现实:1926年10月23日,威尼斯宫。
墨索里尼从漫长的回忆中挣脱,眼前的巴多格里奥、齐亚诺等人还在等待他的回应。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
墨索里尼有些崩溃了,
“你们知道吗……我曾经想成为他们。我写信,我请求,我甚至想买票去柏林……”
“但他们不要我。
葛兰西说我是投机分子,韦格纳连信都不回。而现在——”
墨索里尼猛地抬头,
“现在他们的坦克到了佛罗伦斯,你们却要我去求他们接受?像一条被赶出门又摇著尾巴想回去的狗?”
巴多格里奥愣住了。他从未见过领袖露出这种表情。
“领袖,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就是现在的事!”
墨索里尼咆哮,
“我用了七年时间,建起了这个国家,这个运动,就是为了证明他们错了!证明没有他们那一套,义大利照样能伟大!
现在你们要我承认,我错了?他们对了?”
墨索里尼整个人像被抽空了般跌坐回椅子:
“那我这七年算什么?一场笑话吗?”
许久,墨索里尼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告诉国王,告诉柏林,告诉所有人:
墨索里尼寧可戴著法西斯领袖的面具下地狱,也绝不摘下面具,去乞求一顶他们早已拒绝给我的红色帽子。”
因为他的人生,从1919年那个被拒绝的春天起,就成了一场漫长的、向所有否定他的人证明“你们看错我了”的表演。
而这场表演,必须以他选择的方式落幕——哪怕落幕的方式,是拉著整个国家陪葬。
“出去。”墨索里尼低声说,“都出去吧。”
幕僚们沉默地退了出去。
门关上时,当所有人离开后,墨索里尼独自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望著墙上那张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巨幅照片。
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黑衫军紧紧跟隨著他。
良久,墨索里尼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旧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上面是他亲手写的德文地址:“an den vorsitzenden des volksrats, berlin.”(致人民委员会主席,柏林)
信从未寄出。或者说,寄出了,但永远等不到回音。
他把信封凑近壁炉火焰。火舌舔上来时,他低声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本可以拥有我的,韦格纳。现在,看看你造就了什么样的敌人。”
纸化为灰烬,飘散在威尼斯宫华丽的波斯地毯上。
而在遥远的柏林,韦格纳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这个穿越者建立的红色德国,曾在某个平行时刻,差点接纳了一个叫墨索里尼的义大利人。
而歷史的蝴蝶效应,有时会以最私人化的恩怨,塑造最宏大的悲剧。
第267章 暗流涌动的罗马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