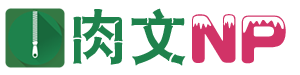神京城,皇宫,文华殿东暖阁。
窗外秋阳透过明黄蝉翼纱窗欞,在紫檀木地板上投下斑驳光影。
天泰帝端坐在御案后,身著一件玄色暗云纹緙丝曳撒,外罩石青色四合如意纹比甲,腰间束著墨玉革带,头上只简单戴了顶乌纱折角向上巾,面庞清癯,双颊微陷,眼角有细密的纹路,但一双眼睛却锐利如鹰隼,此刻正凝神翻阅著案上那叠刚从金陵加急送来的院试复试答卷。
暖阁內极静,只闻铜漏滴水声与纸张翻动的轻响。
侍立在一旁的大太监戴权垂手躬身,白净面皮上神情恭谨,眼观鼻鼻观心,连呼吸都刻意放轻。
天泰帝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份答卷上,许久未动。
那是宋騫的卷子。
字跡清雋工稳,力透纸背,一撇一捺皆见功底,天泰帝逐字逐句读著,指尖无意识地在“外示宽和,內修德政;明察秋毫,静待其隙”几行字上轻轻敲击,节奏由缓渐急,最终停在“慎选贤能,安插要津,如种树然,深根固本,待其成荫”处。
他忽然低低笑了一声,笑声在寂静的暖阁里显得有些突兀。
“好一个『静待其隙』,好一个『深根固本』。”天泰帝喃喃自语,声音里带著一丝罕见的、近乎感慨的情绪,他身子向后靠进铺著明黄云龙纹锦垫的紫檀圈椅里,闭上眼,指尖仍按在那份答卷上。
这些年来,他何尝不是如此?
登基之初,朝局晦暗,江南盐政、漕运、织造,处处盘根错节,他不是不想动,是不能妄动,那些老臣、勛贵、地方豪强,早已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牵一髮而动全身。
他只能忍,只能等——等他们自己露出破绽,等新旧势力自然交替,等像范科捷这样的“树”慢慢扎根,等一个合適的时机。
这份答卷,简直像是窥破了他这些年的心思。
“韜光养晦,以静制动……”天泰帝睁开眼,目光再次落在那清雋的字跡上,眼中闪过一丝欣赏,甚至有一丝找到知音的微光,“此子不过十一岁,竟能有此见识……”
他伸手,从笔山上取下一支御用紫毫,蘸了朱墨,笔尖悬在卷首“溧水县童生宋騫”的名字上方。
案首。
这两个字几乎要落下去。
就在笔尖即將触及纸面的剎那,天泰帝的手忽然顿住了。
不妥。
他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蹙,目光重新扫过卷头上標註的年龄——十一岁,太过年轻,院试虽是童生试的最后一关,但十一岁能过县试、府试已属罕见,若再给个案首……这锋芒未免太露。
天泰帝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身形尚显单薄的少年,因一篇切中时弊、深合圣意的文章名动金陵,甚至传入京城,成为各方势力瞩目的焦点。
讚誉、拉拢、嫉恨、试探……这些会像潮水般涌向那个十一岁的孩子。
他想起自己十一岁时在潜邸的日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些风头,出得太早,未必是福。
更何况……天泰帝目光微沉。
此子既已得他暗中安排科考路径,这份眷顾本身已是莫大机缘,若再给个案首,少年人心性未定,难保不会滋生骄矜之气,木秀於林,风必摧之,这份答卷所展露的见识与心性,值得培养,但更需要保护。
笔尖在空中停留良久,朱墨將滴未滴。
终於,天泰帝手腕微转,笔锋落下,却未在“案首”处停留,而是径直翻到录取名单的末尾,在那空白处,工整地写下了“宋騫”二字,並在旁边批了一个小小的“末”字。
最后一名录取。
既给了功名,全了圣眷,又不至於將他推上风口浪尖,天泰帝放下笔,看著那个“末”字,心中思忖,如此安排,旁人只道是陛下怜其年幼,勉强录取,不会过多关注,而这孩子经此一番,也该懂得藏锋守拙的道理。
他轻轻吐出一口气,正欲合上这份卷子,目光却被压在下面另一份答卷吸引——字跡端正中带著一股利落劲,与前一份的清雋工稳截然不同。
天泰帝抽出那份卷子,瞥见姓名,赵文博。
他本只是隨意翻阅,但读了几行,眼神便凝住了。
这份答卷同样围绕“吏治与民利”破题,却並未停留在“静待时机”“安插贤能”的策略层面,而是笔锋直指更深层处——
“……臣观江南诸业,织造、漕运、盐课,皆沿旧制,如织造一业,官府设局,匠户世袭,物料统购,成品官收,层层管控,看似井然,实则僵滯,匠无激励,则工不精,商无利可图,则货不畅,官唯坐收常例,则弊丛生……臣愚以为,非仅整顿吏治可解,当思变通之道。”
天泰帝的脊背不知不觉挺直了,他向前倾身,將卷子挪到灯下更亮处,继续往下看。
“譬如可仿市舶司『抽解』之制,改官府全盘掌控为『招商承办』『分包定织』,许民间殷实商户承揽部分织造任务,官府定品质、限工期、核成本,余利归承办之商,如此,商为逐利,必悉心经营,改良工艺,督促匠作,匠因计件得酬,多劳多得,亦必用心,官府则脱身琐务,专注督察、抽税,岁入未必减,而弊端可大减……”
“再如漕粮运输,可试行『漕船承包』,择可靠船户,定损补条例,许其自募水手、自管航行,按程核验,依约给值,则船户为保利,必惜船爱人,择佳水道,避风避险,漕粮损耗可降,运期可稳……”
天泰帝越读越快,眼中光芒愈盛。
这已不是在讲“等待时机”,而是在讲如何“创造新局”!不是被动地等旧体系自己崩出裂缝,而是主动引入新的力量、新的规则,去鬆动、去改造那僵化的结构!
“改变生產关係……”天泰帝低声重复著卷中一句点睛之语,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好一个『改变生產关係』!”
他仿佛看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不是费尽心机在旧网中安插棋子、等待內斗,而是直接引入活水,培育新的“网”,让新旧两套体系並存、竞爭,最终让更有活力的那一套自然取代僵死的那一套。
务实,精准,不尚空谈,直指核心。
天泰帝猛地抬起头,眼中那点找到知音的感慨已被一种更强烈的、近乎惊喜的情绪取代。
他重新提起硃笔,这一次没有丝毫犹豫,在赵文博的名字上方,稳稳落下了“案首”两个朱红大字。
笔力遒劲,透出由衷的讚赏。
“想不到……金陵一场院试,竟能出这样两个人物。”天泰帝將两份答卷並排放置,左边是宋騫清雋工稳、深諳“势”与“时”的谋略之文,右边是赵文博直指实务、敢於设想“变”与“新”的革新之论。
一个善守,一个能攻,一个洞悉人心世故,一个直面体制积弊。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在两份卷子间来回逡巡,良久,忽然笑嘆一声:“一静一动,一藏一露,倒是相得益彰。”
剩下的答卷,天泰帝翻阅的速度快了许多。
大多数仍是中规中矩,或空谈仁义,或堆砌典故,偶有几句切中时弊,却也流於表面,再无如宋、赵二人般令人眼前一亮的见解,毕竟只是院试,选拔的是刚刚“进学”的生员,鲜有真正能力出眾、见识超卓者。
批阅完毕,天泰帝將硃笔搁回笔山,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眉心,暖阁內铜漏滴答,已是申时初刻。
他忽然想起什么,转头看向一直静立如泥塑木雕的戴权:“戴权。”
“奴婢在。”戴权立刻上前半步,躬身应道,声音轻而稳。
“林如海家眷,走到何处了?”天泰帝问道,目光投向窗外秋日高远的天空,“算算日子,也该进京了吧?”
戴权垂首,略微回忆了一下昨日收到的驛报,恭声回稟:“回皇爷的话,林盐政家眷自扬州登船,沿运河北上,前日已过沧州,按正常行程,若无风雨阻滯,约莫……还有三四日便可抵达通州码头,再换车马入京。”
天泰帝点了点头,手指在御案边缘无意识地轻叩两下:“嗯,路上可还太平?”
“沿途皆有地方官接送护卫,驛报未曾提及异常,应是太平的。”戴权答道,稍顿,又补充了一句,“贾雨村一路隨行照料,颇为尽心。”
“贾雨村……”天泰帝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语气平淡,“吏部那边,金陵知府的缺,定了么?”
“尚未最终用印,但……如无意外,应是此人。”戴权声音压得更低了些。
天泰帝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目光重新落回案上那叠答卷,特別是赵文博那份,若有所思,片刻,他挥了挥手:“林家母女抵京后,好生注意著,林如海在扬州不易,他的家眷,莫要让人扰了清净。”
“奴婢明白。”戴权深深一揖,“定会安排妥当,请皇上放心。”
天泰帝这才似乎卸下了一件心事,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些许倦色,又带著点完成一项要务后的鬆弛。
他站起身,玄色曳撒的下摆隨之轻动。
“乏了。”他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脖颈,“走,去御苑走走,看看那几笼新进的画眉,还有池子里新放的那几尾锦鲤也该餵了。”
“是,皇上。”戴权忙趋前,小心搀扶。
第94章 意外之喜,赵文博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