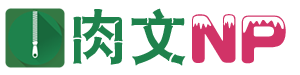第17章:洛阳混战,司马乂掌权司马冏被擒
永寧二年春正月,洛阳城外
洛阳城外的官道上,尘土翻腾。马蹄踏碎路侧残冰,裂出细碎脆响,车轮碾过冻硬的泥垡,轴杆咯吱作响。三千步骑迤邐成线,前锋铁骑已抵护城河岸。司马乂勒马停在一处土坡,抬手示意全军止步,掌心向下,沉凝有力。
他摘下头盔,粗糲的指腹抹了把脸上的灰,指缝间沾著泥与汗。肩甲处渗著暗红的血,粗布裹得紧实,稍一动弹,便扯著皮肉钻心的疼。昨夜急行五十里,士卒脚底磨破者过半,两辆粮车陷在泥淖中,全靠兵卒肩扛手推才拽出来,却无一人喊累,更无一人掉队。
“东门。”他抬手指向城墙,声音沙哑却篤定,“箭楼稀,守兵换防慢。”
副將快步递上千里眼——铜管镶木,前年从西域商人手里换来的稀罕物。司马乂倾身凑近,眯起左眼,透过铜管望向前方。东门段女墙后人影疏疏晃动,每隔十步才有一名弓手探出头,城楼角旗歪斜卷边,像是慌乱间才匆匆掛上。
“禁军六率听他调遣?”他扯唇冷笑,眼底淬著寒,“也就撑个空架子罢了。”
话音刚落,传令兵疾步跑来,单膝跪地:“將军,云梯备妥,火油桶已运至阵前。”司马乂頷首,翻身上马,腰间长刀出鞘半寸,寒芒一闪。
“点火。”一字落下,斩钉截铁。
二十架云梯同时向前推进,木轮碾过冻土,隆隆作响。护城河吊桥未落,士卒们操起长杆,铁鉤死死鉤住桥链,数人合力猛拉,铁链崩断的脆响划破长空。河水结著薄冰,被云梯碾裂,哗啦水声混著兵卒的喝喊,震彻河岸。第一波登城的百人披著重甲,顶盾前行,刚踏上对岸,城头的滚木礌石便轰然砸下,有人当场被砸翻在地,坚盾碎裂成几片,木屑混著血珠飞溅。
箭雨骤至,密如飞蝗,钉进泥土、木梯,发出篤篤闷响。一名伍长攀至云梯半腰,胸前中箭,箭鏃透甲,他闷哼一声,仰面跌下,正摔在火油桶旁,桶身破裂,黑褐色的油液顺著冻土漫开。
司马乂看得一清二楚,眸色愈沉。他甩蹬下马,反手抓起阵前一支火把,焰苗燎过眉梢。“跟我上!”吼声震彻河岸,带著破釜沉舟的决绝。
亲兵持盾围拢,想护他左右,他却拨开盾牌,提火冲在最前。第二轮云梯刚架稳,他已踩著身边士兵的肩膀,借力攀上三丈高的云梯。一支冷箭擦过臂甲,径直扎进肩膀皮肉,他眉头都未皱一下,左手拔起短剑,反手削断箭杆,右手死死扣住女墙边缘,猛地发力,翻身跃上城头。
两名守军提刀扑来,刀风凌厉。司马乂侧身旋避,躲开第一击,手中短剑顺势横划,刀锋精准划开对方咽喉,血珠喷溅在他的甲冑上;第二人收势不及,被他抬腿狠狠踹中胸口,闷响一声,翻下城墙,坠向城下的冰河。身后將士接连登顶,长刀出鞘,白刃战瞬间展开,喊杀声震彻城头。司马乂带人直扑箭楼,將剩余火油尽数泼在樑柱上,火把掷下,烈焰腾起。
火势瞬间窜上房梁,浓烟裹著火星冲天而上,热浪逼得人睁不开眼。木构樑柱噼啪作响,轰然崩塌,砸出一个巨大的缺口。城门內传来慌乱的嘶喊,守军急调兵力堵口,阵脚大乱。司马乂站在燃烧的箭楼上,长刀指向前方,厉声下令:“破门!”
半个时辰后,东门轰然洞开。残存的守军节节败退,退入內巷,沿街垒起障碍,设伏抵抗。司马乂当即分兵:左路由参军率领五百人控制南市,右路由校尉带四百人肃清北坊,自己亲率主力,直扑宫城方向。
火还在烧,风卷著黑色的灰烬满街飞舞,像下了一场冰冷的黑雪。百姓们闭门不出,偶有胆大者扒著门缝探头张望,见是大军入城,便立刻缩回身,將门栓扣死。街面空荡,唯有死马横臥道中,肚腹鼓胀,几只苍蝇绕著尸体嗡鸣,平添萧瑟。
司马乂骑在马上,左手死死按著肩伤,血已浸透裹布,顺著袖口往下滴,在马鞍边凝成暗红的斑点。他却未下令停歇,一路催马前行,马蹄踏过灰烬,留下深深的蹄印。
“齐王府在哪?”他勒住马韁,问身侧的嚮导。
“將军,前头十字街右转,第三个巷口进去便是。”
巷子狭窄,仅容两骑並行,两侧高墙矗立,门户紧闭,静得可怕。走到巷中,前方突然射出三支冷箭,疾如流星。一名亲兵躲闪不及,中箭落马,其余人迅速散开,贴墙戒备。
“有埋伏!”有人低喝。
司马乂抬手,示意眾人噤声,指尖按在长刀刀柄上。他盯著前方的拐角,目光如鹰,低声下令:“扔火把过去。”
两名士卒举著燃烧的木棍,缓步向前靠近。火光照亮拐角,墙根下趴著七八人,手持长矛,脸上抹著灰,一动不动,与夜色融为一体。火把落地,焰苗窜起,其中一人猛地抬头,正要起身发难,司马乂抬手扬刀,短剑脱手飞出,精准钉进那人喉部。剩下几人暴起反扑,早已埋伏在侧的兵卒一拥而上,刀光闪过,尽数砍倒。
清理完伏兵,队伍继续推进。五十步外,便是齐王府的大门,朱漆剥落,门环锈跡斑斑,透著破败。司马乂抬脚狠狠踹开侧门,带人一拥而入。
院內寂静得反常,廊下的灯笼未熄,烛火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映得影影绰绰。寢殿门虚掩著,他抬手推开,亲自上前查看。
殿內空无一人,床铺叠得齐整,案上的青瓷茶具未收,杯中余水尚温,显然主人刚离去不久。
“搜夹壁。”他沉声道。
四名亲兵立刻动手,用刀柄敲打著墙壁,西侧墙角传来空洞的声响。他们挥刀撬开砖石,一道暗格赫然显现,里面蜷缩著一人,头戴紫金冠,身穿锦缎深衣,正是司马冏。
“出来。”司马乂的声音冷得像冰。
司马冏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嘴唇颤著,双手抱膝缩在角落,一动不动。
司马乂跨步入暗格,屈膝蹲身,单手扣住他的衣领,硬生生將人拖出。司马冏徒劳地挣扎了一下,便被亲兵套上铁索,锁链缠颈,哗啦作响,冰冷的铁环硌著皮肉。
“奉天子密詔,討逆臣司马冏!”司马乂对著门外高声喝道,声震庭院,“今罪首已擒,诸君勿惊!”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杂乱的马蹄声与喊杀声,一队禁军残部从南街杀来,举著长戟,直衝府门。司马乂当即下令列阵迎敌,长刀指向前方:“杀!”
双方在庭院中激烈交锋,刀枪碰撞的脆响、兵卒的喊杀声不绝於耳。禁军残部本就军心涣散,不过一刻钟,便溃不成军,主將被生擒活捉,按在地上。
司马乂让人把俘虏押到面前,居高临下看著他:“降不降?”
那人垂著头,牙关紧咬,一言不发。
“降者免死。”他又说一遍,语气未有半分鬆动。
那人猛地抬头,眼中满是执拗:“我只知齐王令,不知其他!”
司马乂頷首,无半分废话。两名士卒上前,架起那人便拖了下去,片刻后,一颗人头被掷於阶下,鲜血染红了青石板。
其余俘虏见状,嚇得魂飞魄散,纷纷跪倒在地,连连磕头。
“现在呢?”司马乂的目光扫过眾人,寒声问。
“愿降!愿降!”眾人颤声应答,面如土色。
“都记下名字,验明身份。”司马乂对身侧的文书说,“押去宫城武库前候命,听候发落。”
他转身看向被缚的司马冏,冷冷吐出一个字:“走。”
一行人押著司马冏出府,沿主街向宫城行进。沿途仍有零星的抵抗,皆被隨行的小股部队快速镇压,无人能挡。抵达南闕时,天色渐暗,暮色四合,將整座洛阳城笼罩。宫门紧闭,守卫早已换上他的亲信,见他前来,纷纷行礼。
他命人打开武库,取出兵符印信,一一验看,牢牢掌控在手中。又让文书擬写安民告示,加盖自己的临时关防,派人分赴各坊,四处张贴。
“放粮。”他对仓官下令,“太仓开三门,賑济百姓,每户限领一斗,派兵看守,不得哄抢,违者按军法处置。”
“將军,是否要即刻通知百官,前来议事?”幕僚上前请示。
“不必。”司马乂摇头,“诸事未定,等明日再说。”
他在武库前搭起帐篷,设下简易帅帐。刚坐下,才发现双腿抖得厉害,肩头的伤阵阵抽痛。亲兵端来热水,替他重新包扎伤口,剪开浸透血的裹布,箭创深得可见皮肉,却未伤骨。他咬著牙,任人清理伤口、敷药、缠布,一声未吭,额角却渗出细密的冷汗。
帐外陆续有將领来报,声音洪亮:“將军,左路已控制南市,缴获兵器若干,无百姓伤亡!”“右路已肃清北坊,收编降卒三百,皆已押至武库前!”“宫城內外营垒均已接管,原有守军尽数缴械,待命听宣!”
司马乂微微頷首,问:“城內还有多少残兵,未归降?”
“回將军,估计不足千人,皆分散藏匿在各坊巷中,多为齐王旧部亲信,不敢露头。”
“贴榜文,明告全城。”他沉声道,“凡弃械归降者,既往不咎,仍可归伍;若三日內仍持兵拒捕,或暗中作乱者,格杀勿论,株连同党!”
命令火速传下,城內巡逻队加派双岗,兵卒持著火把,在街巷中来回走动,火光映亮了冷清的街面。有百姓试探著开门取水,见巡兵秋毫无犯,便敢三三两两齣门,低声交谈,心中的惶恐渐消。
半夜时分,一名老吏摸黑来到帐外,自称原司徒府录事,求见司马乂。他让人带入帐內,老吏躬身呈上一份名册,双手颤抖:“將军,此乃洛阳各营兵力部署及太仓、各坊粮仓的存粮数目,小人私藏下来,愿献与將军,以安百姓。”
司马乂接过名册,翻了几页,字跡工整,標註详尽,眼中稍露讚许。“你留下。”他说,“明日隨我去查各仓,点验存粮,不得有误。”
老吏连连叩首,应声退下。
司马乂坐在灯下,目光落在案上的洛阳地图上,指尖划过虎牢关、滎阳、巩县,每一处都用硃笔標了红圈。他知道,这些险关重镇,迟早要一一掌控,但眼下,最要紧的是稳住洛阳城內的局势,安抚百姓,整肃军心。
他让亲兵取来乾粮,硬邦邦的麦饼啃了几口,就著一碗冷水咽下。烛火跳动,映得他脸上的阴影交错,眉峰紧蹙,不知在思索著什么。他想起出发那日,长沙城外的晨雾,白茫茫一片,也想起路边那个坐在地上哭的小女孩,衣衫襤褸,望著大军离去的方向。
如今城破了,逆臣擒了,仗暂时打完了。
可他心里清楚,事情,远未结束。
他站起身,走出帐篷,夜风刺骨,卷著寒意扑面而来,吹得衣袍猎猎作响。宫墙上站满了守卫,人人握刀,目光警觉,盯著四周的动静。远处的街巷漆黑一片,偶有火光闪动,不知是哪家还未熄灯,或是巡兵的火把。
一名巡兵路过,见他立在帐外,立刻停下脚步,躬身行礼:“殿下。”
“继续巡,仔细些,莫要鬆懈。”他说。
那人应声而去,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夜色中。
司马乂站在武库门前,目光望向南闕下的囚室。那里点了一盏油灯,昏黄的光透过窗纸漏出来,能看到人影晃动。司马冏被关在里面,铁索加身,衣冠不整,却始终没传出半分声响。
他没有过去,只是静静看了片刻,便转身回了帐中。
帐內,他铺开竹简,取过笔墨,写下第一条军令,字跡遒劲,力透竹帛:“即日起,洛阳全城戒严,宵禁时间为酉时至卯时,凡无故外出者,一律拘押,按律处置。”
写完,他盖上隨身携带的私印,朱红的印泥落在竹简上,格外醒目。
放下笔时,指尖发麻,肩头的伤又开始隱隱作痛。他揉了揉眉心,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他知道,明天,会有更多的事等著他。朝臣要见,政令要发,兵权要理,百姓要安。千头万绪,压在心头。
但他別无选择,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帐帘掀开,亲兵送来一件厚袍,轻声道:“將军,夜里凉,披上吧。”
他接过厚袍,披在身上,暖意裹住了些许寒意,却未说话。
外面的风更大了,吹得帐篷微微晃动,一根旗杆被吹得弯了腰,发出吱呀的声响,立刻有兵卒跑去加固,脚步声急促。
帐篷角落,那柄射倒伏兵的短剑斜插在木桩里,剑身沾著的血尚未洗净,在烛火下,泛著冷幽幽的光。
第17章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