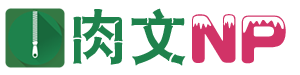1961年的夏天,日头毒辣得有些邪乎。
那太阳掛在天上,不像是给人送暖的,倒像是个烧红了的大烙铁,死死地摁在北京城的脊梁骨上。地皮被烤得泛起一层白花花的盐碱,连路边的野狗都张著嘴,吐著那干得发紫的舌头,趴在阴沟边上一动不动,只有肚子还在那一鼓一鼓地喘著粗气。
南锣鼓巷粮站门口,队伍排得跟长龙似的,一直甩到了胡同口。
几百號人聚在一起,却没什么声响。没人有那个力气閒聊,大伙儿都缩著脖子,耷拉著那颗像是隨时会断掉的脑袋,儘量减少体力的消耗。那一双双深陷的眼窝里,透出来的光是绿的,是饿出来的凶光。
傻柱也在队伍里。
这一年多的光景熬下来,他变了。
彻彻底底地变了。
那个曾经在四合院里咋咋呼呼、一言不合就撩阴腿、满嘴跑火车的“四合院战神”,如今像是一条被人打断了脊梁骨、又拔了牙的老狗。他沉默,阴鬱,走路都贴著墙根,生怕被人踩了尾巴。
他那只断了的右手,因为当初为了省钱没去大医院正经接骨,现在彻底废了。手腕子向內蜷曲成一个怪异的角度,肌肉萎缩得只剩下一层皮包骨头,看著跟个风乾的鸡爪子似的,只能无力地吊在胸前。
身上那件曾经代表著大厨身份、油光鋥亮的白褂子早就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打满补丁的破汗衫。那汗衫原本是灰色的,现在被汗渍和油泥浸得发黑,散发著一股子酸腐的餿味。
“下一个!”
粮站窗口里,办事员那更年期特有的尖嗓门像是锥子一样扎了出来。
傻柱浑身一激灵,赶紧往前挪了两步。他用那只完好的左手,哆哆嗦嗦地从怀里那个贴肉的布兜里掏出两个皱皱巴巴的小红本子——那是粮本。
一个是何雨柱的。
一个是何雨水的。
他把粮本递进去,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那是练了无数次才练出来的“镇定”。
办事员是个胖大妈,虽说现在大家都饿,但粮站的人总归是有油水的。她没好气地翻了翻本子,眼皮都没抬一下,例行公事地问道:
“怎么是俩人的?何雨水呢?这一年多怎么也没见著这丫头露面?这大活人还能凭空没了?”
“我告诉你们啊,街道办最近可是发了红头文件,要严查空掛户!这要是人不在了还在领粮,那可是诈骗公家財產,是要蹲大牢的!”
这一嗓子,把周围排队的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那些目光里有怀疑,有审视,更多的是一种“看你倒霉”的幸灾乐祸。
傻柱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那颗本来就虚弱的心臟“砰砰”狂跳,撞得胸腔子生疼。后背上瞬间渗出一层冷汗,把那是破汗衫都给浸透了。
但他脸上那副木訥、麻木的表情却一点没变,甚至还在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硬生生地挤出了一丝討好的、卑微到了尘埃里的笑:
“哎哟,大姐,您看您说的。这可是我亲妹子,我能害她吗?”
傻柱压低了声音,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雨水啊,她前年就嫁到保定去了。但这户口……咳咳,那边不接收,还没迁走。您也知道现在的光景,那边农村更苦,没定量啊!这丫头在那边活不下去,全指著这边的这点口粮吊命呢。我这当哥的,每个月领了粮,还得托人给她捎过去。不容易啊……”
谎话。
彻头彻尾的谎话。
说这话的时候,傻柱的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这一套词儿,他在心里背了成千上万遍,早就能倒背如流了。
何雨水去哪儿了?是死是活?
傻柱不知道,也不敢去想,更不想去打听。
自从那次他在医院被扔下,这一年多来,那个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傻哥”的丫头,就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刚开始那两个月,他还没在意,甚至还有点庆幸,觉得少张嘴吃饭挺好。可隨著饥荒越来越严重,隨著他工作没了,钱被王大力要回去了,甚至连易中海的棺材本都被掏空了的时候,他突然在那个落满灰尘的抽屉角落里,发现了何雨水的粮本。
那一刻,他眼里的光,比狼还绿。
那是命啊。
那是每个月二十多斤的救命粮!是能换钱的硬通货!
办事员狐疑地看了看傻柱那副残废样,又看了看后面排得老长、已经开始骂娘的队伍。这大热天的,谁也不愿意为了这点破事儿耽误工夫。
“行了行了,赶紧拿走!下回让她本人来……或者弄个证明信!”办事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在粮本上盖了个章,“你也真是个残废命,还得养个外嫁的妹子。”
“哎!谢谢大姐!谢谢大姐!您真是活菩萨!”
傻柱如蒙大赦,点头哈腰地接过粮本和布袋子。
当那两份沉甸甸的粗粮——其实就是高粱面掺著红薯干——落进袋子里的那一刻,傻柱死死地把它抱在怀里,那力度大得像是要把袋子勒进肉里,像是抱著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娘。
他头也不回地钻出了人群,脚步快得甚至不像个残废。
出了粮站,他没有直接回四合院,而是七拐八拐,钻进了几条复杂的胡同,最后在一个僻静得连野猫都没有的墙角停了下来。
那里,早就蹲著个戴著破草帽、帽檐压得极低的男人。那男人一身黑衣,看起来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正警惕地四处张望。
这是鸽子市的“二道贩子”。
傻柱走过去,一句话没说,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没有。他极其熟练地打开布袋子,把属於何雨水的那份细粮(少得可怜的一点麵粉)和大部分粗粮倒了出来,装进了男人递过来的黑布袋子里。
“七块。”
傻柱伸出那只枯瘦如柴的左手,声音沙哑,像是两块锈铁片在摩擦。
草帽男人也没废话,从兜里掏出一把皱皱巴巴、甚至带著汗臭味的零钱,数出七块,拍在傻柱那只像是要饭碗一样的手心里,然后拎著粮食,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了巷子深处。
七块钱。
在这个饿殍遍野的年头,一份完整的城市口粮指標,在黑市上能卖出天价。七块钱,足够傻柱去鸽子市买点高价的烂红薯干、野菜糰子,或者是运气好能买到一块发臭的猪下水,混著自己那份剩下的定量,勉强维持一个月的生存,不至於饿死。
傻柱攥著那七块钱,手心滚烫,烫得他心慌。
这是卖妹求荣吗?
是。
这是吃人血馒头吗?
是。
但他心安理得。
他站在阴影里,看著手里的钱,嘴角甚至勾起了一抹扭曲的笑意。他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一个完美得无懈可击的藉口:
“雨水那丫头,要是还活著,肯定不差这一口吃的;要是死了……那这粮食指標留著也是浪费给国家,不如救活我这个亲哥。老何家就这一根独苗了,我得活著,我得给老何家传宗接代。这也是为了雨水积德啊。”
“呼……”
傻柱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把钱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內衣口袋里,那是他这个月活命的本钱,是他的胆。
没工作,没大席,没人请客。现在的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人。如果不吃这份“人血馒头”,他早就饿死在易中海那间发霉的屋子里,变成一具乾尸了。
整理好衣服,傻柱抱著剩下的那点口粮,拖著沉重的步子,回到了四合院。
刚进大门,一股热浪夹杂著尘土味扑面而来。
前院,阎埠贵正蹲在门口,手里拿著个破喷壶,正在给那几盆早就枯死的花草浇水——其实就是做做样子,显得他还有点文人的雅兴。
阎埠贵这一年更瘦了,两颊深陷,颧骨高耸,跟个成了精的螳螂似的。那副眼镜架在鼻樑上都直晃荡。
听见脚步声,阎埠贵那双算计的小眼睛瞬间亮了,像雷达一样在傻柱身上扫了一圈,最后死死地钉在他手里那个瘪了一半的粮袋上。
“哟,傻柱,领粮回来啦?”
阎埠贵扶了扶眼镜,站起身来,挡住了去路,语气里带著几分试探,还有几分掩饰不住的嫉妒:
“这口袋看著不轻啊……我记得雨水的粮本还在你那儿吧?这丫头一年多没信儿了,这粮食……你一个人吃两份?这不合规矩吧?”
阎埠贵眼红啊。他家人口多,定量不够吃,早就饿得两眼发蓝了。看著傻柱这个废人还能领两份粮,他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
若是放在以前,傻柱早就一口唾沫啐过去,指著鼻子骂一句“阎老抠,关你屁事,滚蛋”。
可现在,傻柱只是停下脚,低著头,那张蜡黄的脸上面无表情,像是戴了一张死人面具,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三大爷,您操心操多了,容易老。”
傻柱淡淡地回了一句,声音低沉,没有一丝火气,更没有一丝以前那种混不吝的劲儿。他就像是一潭死水,扔块石头都激不起半点波澜。
说完,他侧过身,像个没有生气的幽灵一样,绕过阎埠贵,径直往中院走去。
“嘿……”
阎埠贵愣在原地,看著傻柱那佝僂、萧索的背影,原本想好的那些敲竹槓的话都被堵在了嗓子眼。
一阵穿堂风吹过,阎埠贵莫名地打了个寒颤,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傻柱……怎么变得这么阴沉了?跟个鬼似的……这眼神,瘮人啊。”
中院,易中海家。
屋里光线昏暗,窗户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多少光亮,却透著一股子陈年的霉味和老人味。
易中海躺在炕上,身上盖著那床发硬的薄被。他也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一身曾经支撑著他在四合院呼风唤雨的“正气”,早就被这一年多的飢饿、挫折和算计磨得精光。
剩下的,只有一副苟延残喘的皮囊,和一颗更加贪婪、扭曲的心。
听见门帘响动,傻柱走了进来。易中海那浑浊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转了转,像是垂死的鱼翻了个身。
“领回来了?”声音嘶哑。
“嗯。”
傻柱没多话,把那个瘪瘪的粮袋放在桌子上,发出“噗”的一声轻响。
然后,他走到炕边,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七块钱,一张一张地数好,抽出两块皱巴巴的纸幣,放在炕沿上:
“爸,这是这个月的钱。给您买药,或者是买点菸叶子抽。”
易中海没客气,那只手枯得像树皮一样,却以惊人的速度一把抓过钱,塞进枕头底下。
有了钱,即使是躺著,他也有了点安全感。
“雨水那丫头……还没信儿?”
易中海突然问了一句,语气平淡,听不出是关心,还是试探,或者是某种隱秘的期盼。
傻柱正在倒水的动作顿了一下。
屋里死一般的安静,只能听见水流进破瓷碗的声音。
“没。”
傻柱坐下来,端起那碗带著土腥味的凉水,“咕咚咕咚”灌了一口,然后眼神空洞地看著那糊满报纸的窗户:
“没信儿也好。没信儿……这粮咱们就能一直领著。只要她不回来,这七块钱就是咱们的。”
“只要没人去街道办举报,咱们就能活。至於她是死是活……那就是她的命。”
易中海听了这话,在昏暗中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看著眼前这个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些阴鷙可怕的乾儿子,心里反而更踏实了。
以前的傻柱是个炮仗,一点就炸,那是祸害,是惹祸精。
现在的傻柱是个哑炮,虽然不响了,但肚子里的火药更多了,心里的毒更深了。
这才是和他易中海一条心的人。这才是能陪著他在阴沟里打滚的人。
“吃饭吧。”
易中海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硬得像石头的发黑窝头,那是昨晚剩下的。他用力掰了一半,递给傻柱,语气里甚至带著一丝“慈祥”:
“省著点吃,这个月日子还长著呢。这窝头……可是拿你妹子的命换来的,別浪费了。”
傻柱接过那半个窝头。
那是用何雨水的口粮指標换来的钱,再去买回来的劣质代食品,甚至可能掺了锯末和观音土。
但他拿在手里,没有丝毫犹豫,张开嘴,狠狠地咬了一口。
“嘎嘣。”
他嚼得很香,很用力,两颊的肌肉鼓动著,像是在嚼碎什么仇人的骨头。
愧疚?
也许在某个深夜惊醒的时候有过吧。但在飢饿面前,在生存面前,在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煎熬面前,良心这东西,早就被他混著这苦涩的、拉嗓子的窝头,嚼碎了咽进了那如同无底洞般的肚子里。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活著。
哪怕像条狗一样,哪怕吃著妹妹的血肉,也要活著。
只要活著,就有翻盘的那一天。只要活著,他就能看到陈宇倒霉的那一天。
……
后院。
陈宇站在窗前,手里端著一杯刚泡好的茉莉花茶,茶香裊裊。
他透过窗户缝,看著中院傻柱那屋里透出的微弱如豆的灯光,那灯光摇曳著,像是隨时会熄灭。
“吃著亲妹妹的『买命钱』,还能睡得著觉,吃得下饭。”
陈宇轻轻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何雨柱,你这禽兽的境界,算是修炼到大圆满了。易中海那个老鬼,把你调教得不错啊。”
【叮!检测到何雨柱人性彻底泯灭,负面情绪值+500!】
陈宇听著系统的提示音,眼神淡漠。
“在这大灾之年,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了。而傻柱,已经彻底墮落成了这四合院里,最纯粹的那个『恶人』。”
“不过……”
陈宇关上窗户,不再看那令人作呕的一幕,转身走向那摆满物资的餐桌:
“越是疯狂,灭亡得就越快。傻柱,你的报应,已经在路上了。”
第146章 昧良心冒领口粮,活死人苟延残喘
同类推荐:
这些书总想操我_御书屋、
堕落的安妮塔(西幻 人外 nph)、
将军的毛真好摸[星际] 完结+番外、
上门姐夫、
畸骨 完结+番外、
每天都在羞耻中(直播)、
希腊带恶人、
魔王的子宫、